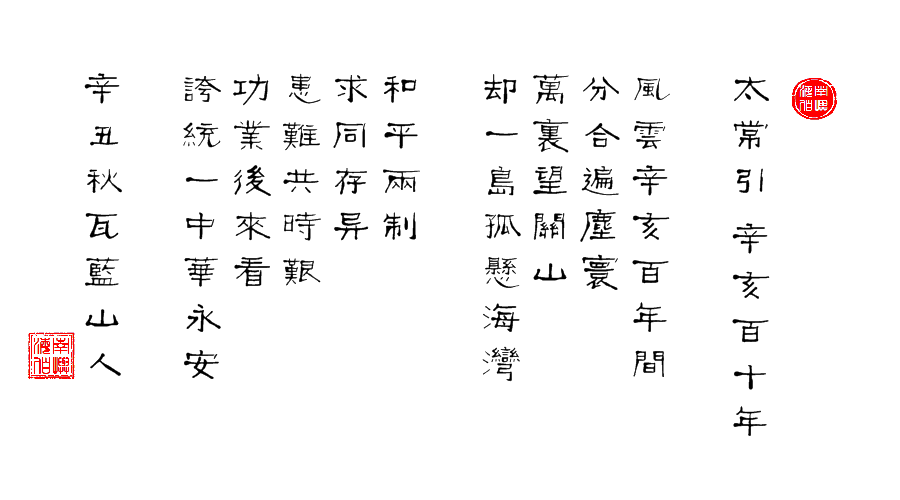入秋以来,好久没有下雨了。今天预报有雨,但是早晨出去,却是一副天晴的样子。直到下午,雨终于下来了。原来,农历今天是寒露时节。
说是到了寒露,蝉噤荷残。今晨散步,见路中有个秋蝉,用脚轻轻一扒拉,秋蝉在地上连蹦带跳地叫了起来。但是,已经飞不起来了,再也不能在树上吸吮着树汁欢唱了。举目望去,近处的枫叶已经泛红,远处树林仍是绿色一片。正如老话说,草木一秋,人生一世。寒蝉不就是人生此刻的写照吗。老生常谈的感叹,接着就是“黑发不知勤学早,看看又是白头翁。”
《脸书》传来”往事回忆“,是六年前的写的一段小文:
月兮星兮橙黄点点游曳
晨兮暮兮蓝黛郁郁云霓
梦兮魂兮靑烟幽幽缥渺
天兮地兮苍茫荡荡神奇
寒露秋雨易伤感 游子海外趋热词
前几年,秋天容易伤感。近来似乎有所改善,大概是伤感过了,不如聊几个热词,换换秋天的情感了。
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此间国内发生了好多新生事物,有的在新闻和媒体上看到,有些由于各种原因就没有注意到。就拿眼下流行的“热词”来说,大部分还可以意会,有些词却是摸不着头脑。
比如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与当前的抗疫有关,可以理解为中国政府在抗疫过程中的立场。至于“逆行者”如果不是听说过抗疫过程中,尤其是武汉封城期间,那些迎难而上、不惧风险的人物和群体,大概不容易明白其中的意思。逆行者除了包括医护工作者、解放军、消防员和公安干警这些群体,还有在疫情中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的人们,包括快递小哥、保安、环卫工人、在社区执行管理检测、为居民订菜送饭倒垃圾的志愿者们。
每次大的事件或者灾难来临,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性在其中清楚地展现,既有英雄无畏的大爱,也有卑劣可耻的小人。我们为“逆行者”们的无私奉献而感动。
跟“逆行者”比起来,“躺平”者就消极多了。一个是逆流而上,一个是就地躺平。躺平主要是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想法,产生于当下的社会压力和竞争太大,如就业、职场、住房、生育等等。他们或逃避竞争、降低生活欲望,或不想工作、回家啃老。
他们认为躺平是一种与世无争,无欲无求的人生处世哲学;有人认为躺平是对社会快速发展的无奈选择;有人认为躺平是为了释放情绪后更好地站起来等等。对于躺平这种看似简单实际背后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能一概认为逃避和精致利己主义。固然,逆行者是我们社会提倡的“高大上”,但是,也大可不必指责选择躺平生活方式的人们。大凡社会现象通常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原因则深潜在表象下的社会生活中。
还有一个新词“内卷”,指内部竞争,跟躺平一样,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状况。通常是指那种非理性内部竞争,或是“被自愿”竞争,个人努力遭受通货膨胀等等。
比如学生面临成长压力,在高度竞争中,同伴彼此PK。家长们望子成龙,谁都不愿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拼爹、拼妈,还得拼校外功夫,如培训班、学区房排位赛。资本操作也应运而生,各种线上线下教育培训机构“野蛮生长”,教育沦为商品。
“内卷”已经不再是年轻人,涉及到儿童,中年,甚至老年。不仅孩子累于“内卷”,还有家长。“内卷”不仅内卷走了钱包,也卷走了亲子时光。
对此,现在中国政府采取一个叫做“双减”的政策。一方面,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另一方面,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比如在资本链上开刀,把补习班之类的培训机构一锅端了。
我在想,当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也有同学们之间的竞争,比如考试争第一。这种竞争,跟当时提倡的“力争上游”一样,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受到鼓励的。而且,也不涉及到家长、资源和资本的运作。为什么今天社会进步了,资源丰富了,反倒“内卷”了呢?难道跟“资本”有关吗?
还有一个“凡尔赛”,一听就会联想到法国的凡尔赛宫,用豪华形容还不够,恐怕要用奢华来形容。近些年,由于中国有一部分人富裕了,随之产生了一批“土豪”们。土豪们爱炫富,被社会所不齿。于是乎由明目张胆的炫,演变成欲盖弥彰的炫,用“凡尔赛”来表示。
比如,有的人为了炫耀自己有钱,就会说,“我最近不得不搬家,因为有私人车库的别墅才有私人充电桩,我家的特斯拉才能用”;还有的人炫耀自己出境游,发帖“今晚我要去维多利亚港哭,以后努力赚钱去巴黎哭。”以一种故作委婉、先抑后扬的话语方式,炫耀自己精致优雅、与众不同。种种“凡尔赛”,在社交媒体评论区里引起各种羡慕、嫉妒、还有愤恨。
在我看来,对于这种人和风气,应予鄙视。或者,以鲁迅先生的轻蔑方式来对待。“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让“凡尔赛”们碰到“无言”和“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上面提到的一些热词,基本上都能猜蒙到八九不离十,只是有个“饭圈”不太明白。经查,饭圈指娱乐业粉丝组成的圈子。怪不得,我对国内的娱乐圈既不适应,也不感兴趣。
饭圈文化是娱乐圈过度商业化、资本化的扭曲反映。具体指的是一些明星为追求流量,通过互联网平台、商业炒作,误导粉丝疯狂追星模仿,导致粉丝中模糊身份认同者有之,散尽家财者有之。种种混乱之后,跟“内卷”一样,是幕后资本主导的一条利益链。
最近看到,中国政府开始整治一些明星和互联网平台了。
人民生命应至上 大使民众试交心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上述的这些“热词”(buzzwords),多半已经在网上流传一段时间了。但是,却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美国的一个“旅游和人文交流”会议场合提出来,并借此向美国公众介绍了中国的最新发展情况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记得从李肇星大使开始,我见过历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多是前辈和平辈,从跟他们的交往中,了解他们的工作作风。离开华府后,秦刚是第一个新任大使。从年龄上看,他属于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值此中美关系极为重要又十分微妙的时刻,有些点担心他属于外交部门的战狼,处理不好眼下的中美关系。
从他到美国来的讲话和行动中,我觉得他不是战狼似地宣战,而是通过各方面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动态和形式,来做好民间的工作:既讲“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逆行者”、“双减”,又讲“内卷”、“凡尔赛”和“饭圈”。还有一次借打趣透露,在成为驻美大使赴任前,他在即将开放的北京环球影城乘坐过山车的经历。当时邀请方有些犹豫,问秦刚是否真的要坐?秦刚的这段回答,颇有深意。
“我说:必须的!这是我做中国驻美大使前的最后一道考验。于是我就上去了,过山车大起大落,急弯倒挂,让人十分紧张,但我都能承受。最终,过山车稳稳地回到了最开始的轨道,平稳着陆,我也通过了驻美工作前的最后一道考验。所以,我来了,与你们共克时艰!”
我看到,这个小秦大使给华府的外交工作带来了一点新气象。期待他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的过程中起到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