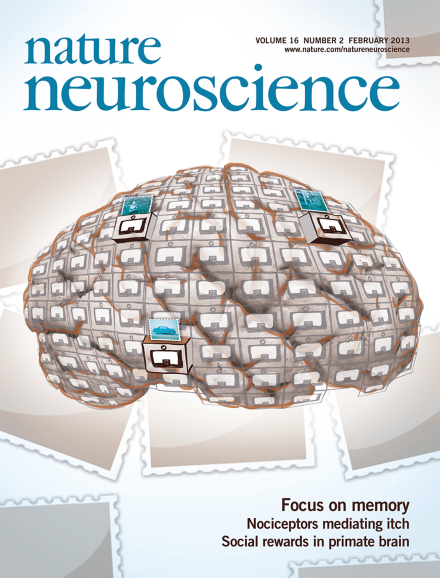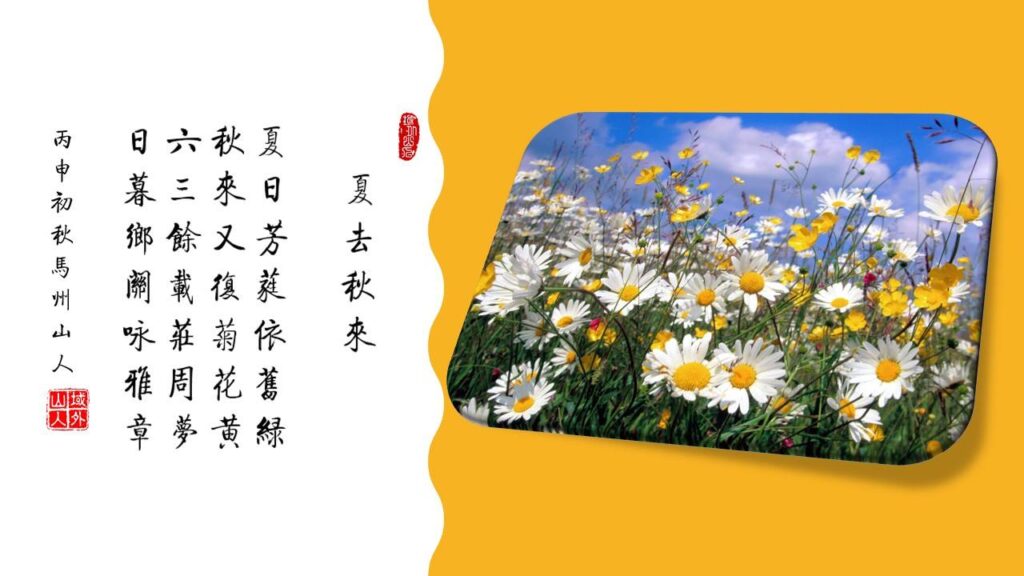飓风过后,早晚的气温开始从90多度下降到80多度,明显的凉快了。傍晚的游泳池凉风习习,出水后身体感到晚风的凉爽。上午到健身房锻炼,一路上来来回回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邻居们相遇,都相互称赞“今天真是一个好天气”。
读书,读一本有关我们这一代的人的书——《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这是一部同龄人书写同龄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六十年经历的书,于2011年出版。自然引起我,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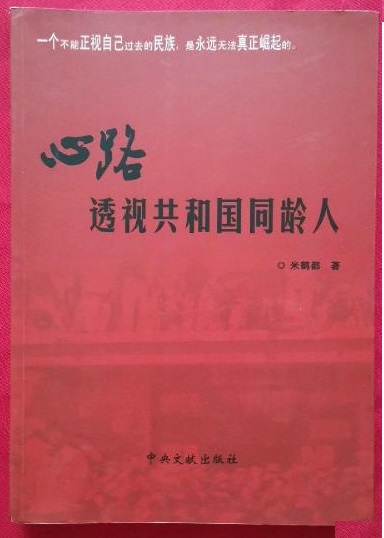
作者米鹤都,1952年出生,是同龄人中跟我比较接近的。我的小学同学中,年龄大约跨越三个年龄段,从1952年到1954年,其中以1953年居多。不同的是,他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比我高一届。这一届之差,就把我们的人生轨迹从中打乱。其实,我也可以属于1968届初中毕业生。
在1960年代,武汉市除了小学6年级+初、高中6年级的“12年制”,还试行一种小学5年级+初、高中5年级的“10年一贯制”。也就是说,大学前的教学分成两个轨道,分别为10年以及12年。据说,“10年一贯制”是一种实验,从前苏联借鉴而来。不知道是不是“伟大导师”心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实验的开端。
我从幼儿园“毕业”后,我们那一届同学大多都被分配到一所试行“10年一贯制”的“鄱阳街小学”,校址就在当年中共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会址的同一条街上。如果沿着这个“10年一贯制”的教学轨道走下去,我就应该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跟我同住一个大院的邻居“发小”,就是从鄱阳街小学毕业,比我提前一年进入初中。其实论年龄,他还比我小一岁。看到他佩戴中学的校徽,而我还是一个小学生,记得当时多么的嫉妒和愤愤不平。
但是,由于我不记得的原因,大概因为我小且调皮,母亲决定将我换到一个“12年制”的“黎黄陂路小学”。可能还有姐姐在黎黄陂路小学,可以顺路带我去上学的缘故。这样就造成了我们同龄人的分道扬镳。1966年文革开始,阴错阳差的我就成了1969年初中毕业生。
1968年,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届初中毕业生到1966届高中生,一共6届中学生,统统离开所居住的城市,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了。从那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历届中学毕业生年复一年地走着上山下乡的道路。
历史的长河一往直前,浩浩荡荡奔泻千里,碰到崇山峻岭也会转个弯,有时候会产生回流,并在不经意之间留下几个漩涡。严密的逻辑和规律定理,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因为从“10年一贯制”的轨道拐到“12年制”,我没有像我的哥哥姐姐,赶上1968年全中国轰轰烈烈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

1969年,等到我毕业时,中国的一些省份出现了在应届毕业生中招一部分高中生的政策,招生的比例时应届生的20%。因着这个年份和这个政策的产生,我成为了那个20%的幸运儿。不记得这个政策产生的前因后果,也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有几个省市试行了这个政策,我只知道湖北省是其中的一个。
很奇妙的是,我的高中就是在“武汉实验学校”开始的。而武汉实验学校就是当年“10年一贯制”的典型实验样板。武汉实验学校包括幼儿园部,小学部(5年)和中学部(5年)。混沌中从离经叛道开始,冥冥中我又回到了原轨,那时的高中学制为2年。
1969年以后,中国开始全面初中升高中的制度。同一个时代,一念之隔,作为的同龄人的作者和我就这样开始各奔前程,一个上山下乡到陕北地区,一个留在城市上学。
作者后来参军入伍,离开农村。参军是文革期间青年人的向往,一个是军队在当时的威望,二是参军可以避免上山下乡,三是在部队里容易入党提干,复员转业后,能回到城里,找个好工作,混出个好前程。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是比我们低两届的同龄人,就是想方设法地参军入伍,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得以施展他的写作才华。
上高中时,有许多同学都不再读书参军进去了,海陆空各军兵种都有。当然,我也很想去参军,圆一个梦。如果我当时参军了,我可能又和作者回到同一个轨道上来,当然也可能从此与大学无缘。不过,我父亲当时不同意我去当兵,大概是我哥哥上山下乡后,已经在当地参军入伍,父亲不想我们俩走一条路,希望我继续学业,将来也许能一文一武?
同样的大时代背景,因为机遇的不同,个人的背景和抉择不同,人生的道路便产生分歧。后来,也是作为试点,我侥幸以5%的几率,直接从高中进入大学,也是因为是文革首届高中生的缘故。人生会遇到各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机遇。假如,当初我母亲没有将我从10年制改为12年制的学校,我就不会赶上应届生升高中的机遇;假如,我父亲同意我在高中时去参军,我也不会碰到高中生直接升大学的机会。
作者的简历,据《百度百科》记载,1974年-1977年上大学,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中共党史专业。其它地方有的记载为1978年-1982年入学。这段学历的时间差距不是简单的74年与78年之间的4年之差,而是文革中未经考试的“工农兵”学员与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经考试入学的本科生两者的差别。这两者之间的语焉不祥,让人觉得作者似乎是个工农兵学员,正如我一样。不过,听说中国人民大学(人大)在文革中经历了1970年停办与1973年解散,知道到1977年才复校招生。按道理讲,作者应该是文革后的大学本科生。
时间进入1970年代后,时代的洪流,又把我们这些分岔的支流汇拢在一起。如果作者是1974年进入大学,那他就跟我一样,是所谓的“工农兵”学员中的解放军学员,尽管我是一个直接从高中升入大学的“假”工农兵学员。总之,到文革结束的1970年代末期,我们的人生轨道又在大学里相遇。
毕业后我在大学任教,作者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等专项研讨。
进入1980年代后,跟大部分同龄人大学毕业生一样,我们同在1988年后出国留学,同在美国学习研究。获得学位后,我同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他同另一部人留学完后海归。
大浪淘沙。回过头来看,每个人的遭遇都有不同,但是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摸爬滚打出来,相互理解熟悉。同龄人讲同龄人的故事,比较真实。如果同龄人写同龄人的那段历史,就是两回事。因为我们没有跳出来,跟历史拉开足够的距离,会有当代的代入感,无法避免亲身经历所长生的感情色彩,很难做到客观。
但是,我们经历过那段历史,有其自然的真实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拿起笔,在历史上留下真实的一点,那么,我们的后人会更真实的了解到共和国的同龄人这段历史,会更如实和客观地了解到我们这代人。

浪花,是大海真实的体现,但不是真实的大海。
09/03/2023 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