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散步,不觉又是周一,一周过得太快了。而且,今天是五月最后一天,一个月也轻易过去。回顾搬到佛州,已三年有余。再回溯,过六奔七,70后在向我招手。很容易就想到“人生七十古来稀。”
顺便重读杜甫《曲江二首》,让那句话回到诗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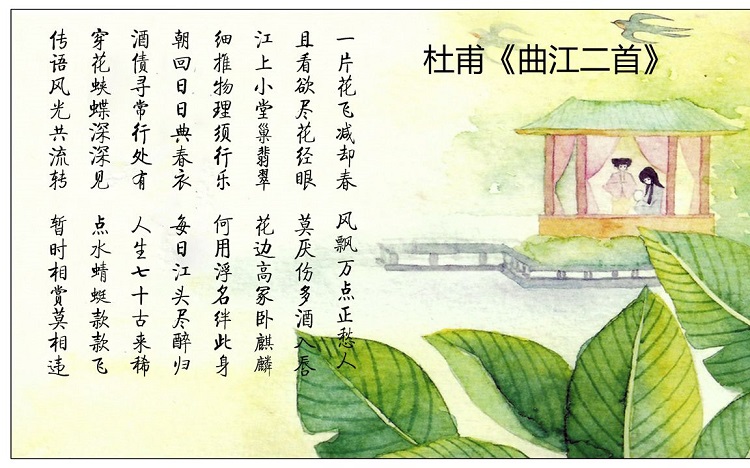
其 一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其 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看诗中所写,应该是暮春浅夏,一片花飞,风飘万点之际。和我们佛罗里达的此时应该很接近。诗人这里有些伤春,万点飞花在他的眼中是减春和愁人。把花看尽了,伤感太多,借酒“入唇”。远眺江上,小堂筑起了鸟窝,园边坟前麒麟(石雕)卧地,往日繁华不再。其中道理,仔细想来,触景伤怀。还是及时行乐,不要追求什么“浮名”的羁绊。
真的不为功名吗?那又为何日日去上朝,不学介子推和陶渊明隐居呢?其实,花飞、小堂、高冢就是作者或者世人的苦苦追求。现在看来,即使追求到了,后来不也是鸟巢筑起麒麟卧地。但是,当时不追浮名,后来又怎么知道是浮名呢?
每天上朝回来,就要典当春衣,真的是食不果腹活不下去了吗?No!其实是为了买酒,买醉。不过,那时的官员真的很穷啊!不但不能吃请,连喝两口小酒要自己掏钱,还要典当衣服。甚至走到哪里饮酒酒债就赊欠到哪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就那副模样么?
酒酣之余,醉眼里花间蝴蝶水面蜻蜓,那种深深和款款的姿态,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于是乎,与春光中结伴而行,及时行乐风流,哪怕时光短暂也不要错过欣赏良辰美景(那才是诗圣的朋友诗仙向往的境界啊)。
真乃春光无情人有情,以情观物物有情。不过,诗句虽美,诗圣在此的意境却是不太高。春天虽美,仅限于借酒浇愁及时行乐。要是诗仙来谈酒,那就牛逼了。“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听说,诗人的仕途状况后来不妙,不多久被贬职,一年后就辞官了。
不过,诗圣的这首《曲江二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或者不记得了。只有这句“人生七十古来稀”却琅琅上口地被老百姓流传了下来。写这首诗时,诗人才四十多岁。为什么诗人这里要用七十岁呢?仅仅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吗?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怎么理解的。不过,如果这句话在诗里面按字面意思理解,总感到有些突兀不合群。怎么就从酒债一下子就跳到年龄上去了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据《礼记·曲礼》记载,人在四十岁时,身强力壮,是出来做官(仕)的时候。而七十岁的时候,就老了,该“传”位,光荣退休了。如果官至“大夫”(宰相、总理、部长),则可以继续留任。是不是很象中国大陆现行的干部退休制度?
所以,”人生七十“意味仕途的巅峰。七十岁之前,是奋斗博取功名的时期,之后则意味着功成身退。想想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古代令人向往的境界。对于一个有抱负有追求的古代读书人来说,官至大夫,荣归故里,是当时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能到达这一高峰的却是寥若晨星的“古来稀”。
以诗人当下典当春衣付酒债的窘境,何时才能达到这个境地?这恐怕才是诗人的感慨。穷困潦倒、典衣赊账,当时是平常可见、到处都有;而人生七十、出阁入相、锦衣玉食却是古往今来人间少有的。也可以说,这是诗人,或者世人,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轻。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进一步说,即使到达这个显赫的高峰,也不过花飞花落、人去楼空、鸠占鹊巢、麒麟卧倒,到头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就是,春夏秋冬,无非就是一个无止境循环往返,一个“永劫回归”的虚无境界。
当时,不知诗人是否悟到这个境界?介子推当年“割股奉君”,并不以此“携功要君“,却淡泊功名,归隐山林,应该说是达到了这个境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算有了这个境界。从诗中最后一句“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来看,似乎诗人此刻采取的还是积极“入世”的态度。
其实,“入世”和“出世”,只是人们认知世界后形成的一个观念,各人按此走完人生,本无所谓对错。
《礼记·曲礼》摘录:
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以其制。

今天晚上是俱乐部麻将牌时间,因此不游泳。不过看到一个跟游泳有关的故事,值得一记。
我们佛州有个沿海的大城市,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一个父亲将带着两个孩子带到船上玩,然后让孩子们下水游泳。大的孩子是儿子,7岁,小的是女儿,才4岁。突然水流一下将女儿冲走了,父亲下水去救女儿,同时告诉儿子自己往岸边游。这时候我们不管为什么父亲不开船去救女儿,为什么不把儿子弄到船上安全的地方,只说儿子这一头。据报道这个7岁的小男孩花了一个小时才游到岸。他表示自己利用仰面漂浮、小狗划水移动,这样就不会筋疲力尽。
这段距离有多远不知道,但是却花了孩子一个小时才游到岸边。当小男孩到达陆地后,又马上跑到最近的住家寻求帮助。根据杰克逊维尔消防和救援部门(JFRD)的说法,父亲和女儿最终漂流到离船的位置大约一英里半到两英里的地方。最终这两个人被成功救起,而年纪虽小却沉着冷静的小男孩也被视为大英雄。
在水里游一个多小时,对于我们每天游泳的人来说,都知道是很累的一件事。一般人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是一个孩子。此事至少说明一件事情,会游泳不仅不会被淹死,还有可能救别人,哪怕是个7岁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