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脸书寄来”你的脸书记忆“,是两年前佛州当日写的小诗,比较典型的佛州夏季雷雨天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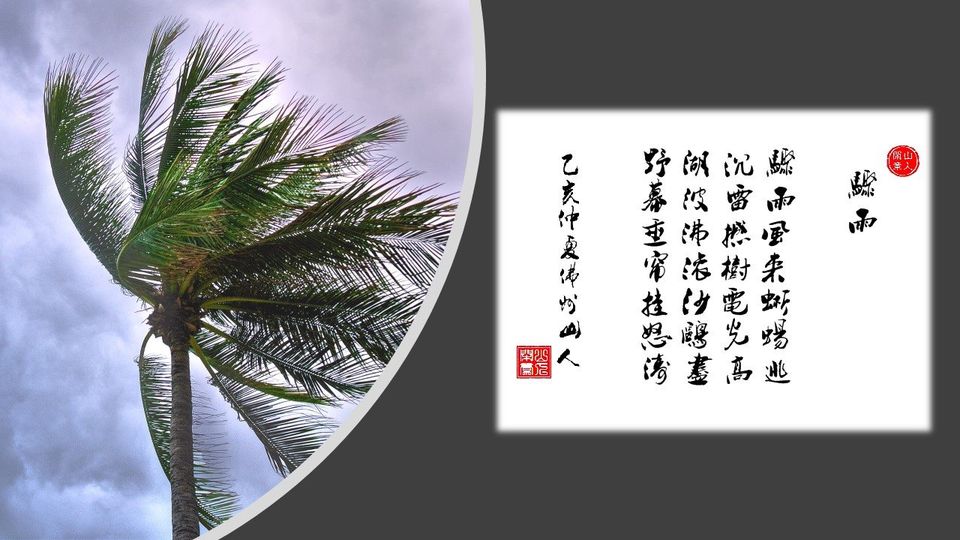
今天转晴了。一大早出门看到小区的四个邻居分别遛着四条狗,一个星期都没有这种不下雨的早晨了。在家中憋了几天的人们,一放晴,就都出来了,当然,还有他们的狗。
左手隔壁的邻居原来是个亚裔,越南老太太,有一只小狗。老太太没有事,常常敲门过来,送些越南食品,然后聊一会儿天。从闲聊中得知,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越南人。她以中国人为自豪,虽然按中国的父系关系讲,她应该是华人,可是却讲不了几句中文。她的丈夫是个美国空军军官,现已去世。她有两个女儿,老大一家四口人原先也住在我们小区,隔我们几户人家。后来,在我们社区外买了个大房子,搬出去住了。小女儿从军队复员后,也住在我们社区外面不远的地方。
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老太太看起来挺硬朗的,每天早上起来浇花,遛狗。近来不小心摔了一跤,趴在地上半天,也没有人知道。大女儿觉得不放心,就把她接到家去了。我们对面的邻居,也是一位老太太。我们刚搬来时,她还颤颤悠悠地过来,送点心表示欢迎新邻居。过了一段时间,就看不见人了。偶然碰到她女儿过来清理房屋,才知道也是女儿把老太太接走了。后来,她们都把房子卖了。
人老了,最好不要孤独。就像杨绛一样,女儿和先生都先走一步,只剩下一个人。好在她身子骨还硬朗,能够照顾自己,能够在孤单中生活,还活了100多岁。其实,隔壁的越南老太太不愿意到女儿家去住,宁可自己一个人住。但是,最后没有办法了,还是得走。看着她们的离去,不免有些悲哀,是为她们,也是为将来的自己,总有一天。
隔壁的新邻居是一对美国夫妇,看起来比我们年轻,有一辆十分惹眼的红色吉普车。他家有一只收养的流浪犬,右前肢没了,只有三条腿,竟然也能走路。那是一只具有哈士奇血统的杂交犬,像一只半大的灰狼,常常卧在门口的草坪上,有时候还会像狼那样对天嚎几声。周围邻居的狗,多是小型狗,都不入我的法眼,唯有这条三只腿,还有点狗样。邻居们在一起聊天时,它似乎也不跟小狗们在一起凑热闹。
小区的周五,就在邻居们互道早安和爱犬们呜呜汪汪的欢叫声中开始了。
昨天看欧洲,今天回到中国的《纸年轮》。到了80年代,一个我应该熟悉,但是又似乎陌生的年代。
1980年代的第一本书《围城》,我没有看过,却听得耳朵可以起茧。《围城》最早是1947年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80年之前似乎没有再版此书。怪不得年青时如饥似渴想读书时,都没有听过此书。
据说,旅美的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围城》以很高评价,引出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他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当是见道之言。这才引起国内读者再度注意,并且再版。
听说此书刚出时,褒贬都有。有人讥讽《围城》是“香粉铺”、“活春宫”。这类负面评价引起了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家巴人先生的愤慨。他在报端发表文章说,谩骂《围城》的人不是共产党人,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表该文。据说巴人这篇文章一出,讥讽、批评《围城》的人立时“偃旗息鼓停止攻击”,其威慑力相当可观。
我没有看过该书,没有发言权。只是巴人先生拿共产党人的大旗,作为评论的标准——虎皮,使得讥讽、批评《围城》的人立时偃旗息鼓。如果真有此事,不免感到有些“霸道”。共产党人的东西就不能批评么?况且作者钱钟书也并非共产党人啊。
虽然没有看过此书,也没有想看此书的兴趣,不知道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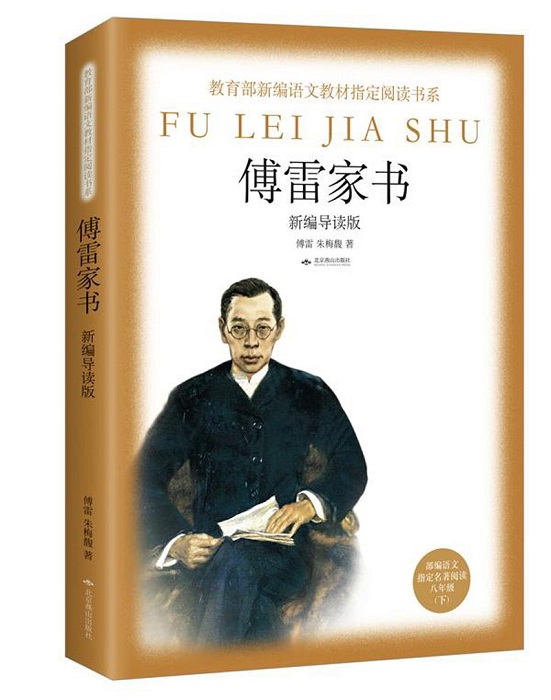
1981年出版的是《傅雷家书》,也是一本耳熟能详却无缘读过的书。书中傅雷写信时,录下这段话:“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并称“这是我们固有文化中的精华,值得我们自豪的”!表示这种状态是自己“一生向往的境界”。
尤为珍贵的,是书末所收署名“傅雷梅馥”的绝命手书。毛笔,竖写,没有一丝仓促气息。在身后委托的十三件事情中,所有涉及现款及存单的项目,其序号上面均划有“√”符号,明显是逐项写下数目后,如数放妥,一一核实,确保无误,不欠世间分毫,才把谢世的绳索套向自己的脖子。
看到此处,不禁仰天长叹,眼睛开始有些湿润。有机会一定好好读一下此书。
1982年出的《世界史纲》没有读过。那个阶段,好像我陷入英文学习和教学中不能自拔。本书译者为“吴文藻等”,被“等”进去的人有谢冰心、费孝通这等名家。一次闲谈中,费先生曾说到人的才学。他说:我的上一代人,如梁启超、梁漱溟这一辈,他们才也高,学也好。到了我这一代,才还有点,学就不行了。再往下的人,该念书的时候没有正经书可读,更不用说了。
唉,我就是那些“更不用说了”之辈。因此,看到1985年出版的《宽容》一书,我连听都没有听过,但是惭愧感似乎少了些。
经查,作者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的书在美国十分畅销,拥有惊人的销售量。但在历史学研究上,房龙则并未取得相应的学术地位与成就,基本上是被定位于一位“优秀的通俗历史作家”。
中国当代作家郁达夫曾评价说:“范龙(即房龙)的这一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范龙的笔,有这一种魔力。但这也不是他的特创,这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以讲述科学而已。”
经这么一讲,我开始对房龙的书感兴趣了。因为我读史书,并非做严谨的历史研究,只是想通过故事来了解和记住历史,文学性越强越好。比如读过小说三国,我记住东汉末年有三国之乱;然后汉朝亡了,三国归晋;也知道了“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还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
1986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也是我未读之书。我是从读费孝通先生的文章中,知道这本书的。严格地说,这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的英文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该书在世界上大有名气,但是直到80年代才被人译成中文出版。两种语言文本,隔着近半个世纪沧桑。作者以五言诗的形式写下如此感慨:
愧赧对旧作,无心论短长。
路遥试马力,坎坷出文章。
毁誉在人口,浮沉意自扬。
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
岁月春水逝,老来羡夕阳。
盍卷寻旧梦,江村蚕事忙。
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写于1978年。他以古稀之龄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开专栏,取名“随想录”。这次艰难、漫长、壮丽的思想跋涉,中间受到攻击和批判,持续到1986年秋。从首篇《谈〈望乡〉》到终篇《怀念胡风》,共百五十篇,逐篇见刊,陆续结集。作者视此书为自己的“文革博物馆”。可惜我没有看到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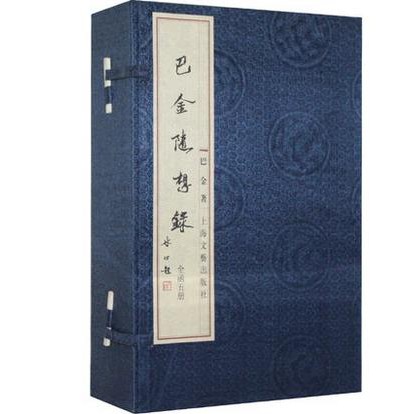
写出此书后,巴金先生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我们呢?我们也能心安理得么?我们还有对心的看重、对理的尊重么?
1988年的《山坳上的中国》和1989年的《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都没有读过。看到此处,才发现,80年代出版的这些书,听过的大概有3、4本,读就“更不用说了”。其中,有些已经时过境迁,没有现在读的必要了。其中有几本经得住时光考验的,倒是值得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