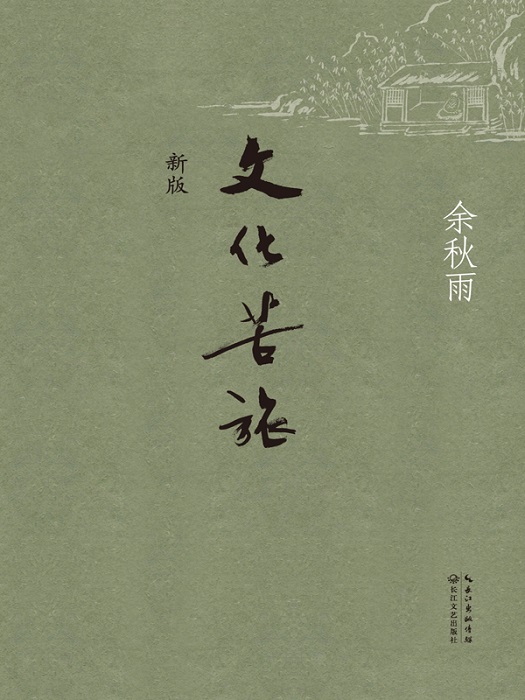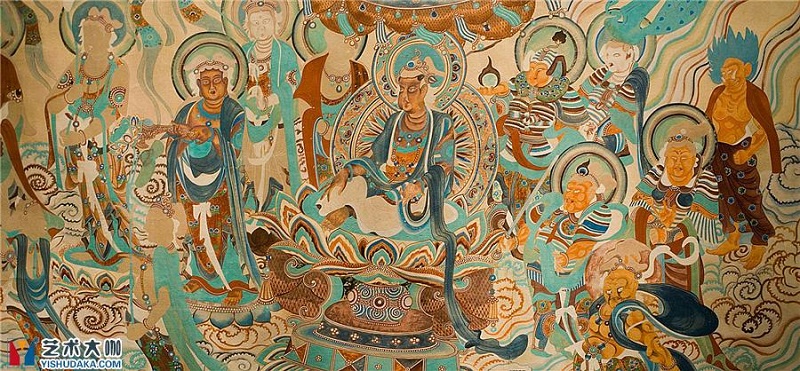头上的云层,低低的,薄薄的,轻快地在蓝天飞过,像薄纱被风吹开了,漫无目的地飘,很快就消失在蔚蓝色的无际。再往下,是树枝的摇摆晃动,一排排早操中绿色的手臂。还有军人纪念园中,几面色彩鲜明的军旗在猎猎作响。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邻居门前的风车,一阵阵急促地飞花乱舞,让平静的社区感到年轻心脏的跳动,仿佛小鹿乱撞青春的荷尔蒙。
一阵不经意的空气流动,自然界再普通不过的寻常,也会撩起旗杆上平静多时的旗帜,展现出上面平常掩卷的图案和字母,并让它们在阳光下鲜艳明亮。若是此刻人们正好身心感受,是否心中也会荡起微澜?
没有风,自然界会显得太平静,人们会无聊至死板。微风徐徐,令大地风情万种,使得人类遐想无限。可是,风大了,又令人担心,尤其是形成龙卷风,摧枯拉朽,毁灭掉地面一切有形之物,又过分得冷酷无情。人类怎么就这么矫情,弱不经风,冷热不得,非取中庸?
三国曹操天时占 八十万众化白旗
风大了,惹不起,还是回到小小不起眼的病毒上来看看。
新冠病毒变种“奥秘克隆”Omicron。从南非发现以来,至今已有月余。人们开始逐渐了解这种“奥秘”是怎么“克隆”的了。传播快是Omicron的特征之一。
根据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统计,奥秘克隆迅速攻占全美至少33州,约3%添加确诊为Omicron所致,联邦高层官员14日警告,Omicron可能很快成为美国主流病毒株并引发大波疫情;而全美过去两周添加确诊暴增近50%,最快恐在1月达高峰。
纽约时报统计,美国新冠病毒13日单日添加确诊12万例,过去两周暴增49%,病殁人数则增加1276人,过去两周攀升40%。对此,许多州也纷纷实施防疫限制,盼能围堵“奥秘克隆”。加州和纽约州陆续恢复室内口罩令,费城和纽约市居民得提供疫苗证明,才能进酒吧和餐厅。我们佛罗里达照样处变不惊,似乎州长大人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措施。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统计,截至14日,全美新冠病毒确诊逾5022万人,逾80万人病殁。八十万人就这么没有了?想当年,曹操领兵旌麾南指,治水军八十万众,邀孙权会猎于东吴。何等的耀武扬威。而孙、刘联手,周瑜、诸葛亮赤壁火烧连营,又何等的精彩。如今,美利坚合众国八十万众,新冠病毒之前,竟然化作华盛顿国会山下一片白色旗海,微风中瑟瑟无言,何等悲哀。
然而,曹操毕竟占有天时,终是灭了吴蜀。今日之美国,仍占天时乎?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特斯拉汽车公司总裁马斯克(Elon Musk)在回答关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提问中说到:在任何人最久远的记忆里,美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那可以追朔到一个世纪前的120到130年。世界上已经没有这么长寿的人,可以记得美国还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代了。我们正处于这么一个时代:中国的经济力是美国的两到三倍,这是一个不可同日而语的世界了。
他还说:中国人曾经以一个小经济体的角色被人呼来喝去,他们恐怕还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是这个街区最靓的仔(the big kid on the block)。一旦成为这个街区最靓的仔,那么,你就真的可以对各种事物保持冷静。你就不必担心,因为其它国家对你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是一个重要的心态改变。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也是这么认为,并拥有这个靓仔的心态?至少,目前国人尚无。
中国,在马斯克眼里,俨然已经是一个区域中的靓仔了。他希望中美这两个不同街区的靓仔能够合作,毕竟我们都是人类的一份子。上个月,马斯克在推特(Twitter)上引用曹植《七步诗》,一时间引起轰动和许多猜测。我想,希望美、中两国如兄弟一般和睦相处,而不要骨肉相残,大概是其中的用意之一吧。
但愿,但愿!
古塔开封召后代 兰州牛面白兰瓜
看到有位中学生读《文化苦旅》后的调侃。从此,他的作文里有一半的篇幅是排比句,平均每千字要惆怅5次、叹气4次、掩卷沉思3次、潸然泪下两次、问苍茫大地一次。作文从此自然是“横扫千军如卷席”,连高中部的学长都不是他的对手。(一笑)不过,也可以算是对余秋雨文风的一个段子。
从大西北狼烟滚滚的苍凉大梦中醒来,余秋雨又进入中原厚重大地和南方灵巧湖泽的细腻人文之旅。从我所读的版本看,大约他的步履止于《五城记》。
五城中,我到过南京、成都和广州,虽然大多是匆匆路过,宛若惊鸿一瞥。而中原腹地的开封和西北一隅的古城兰州,却至今尚未曾谋面。
老态龙钟的开封府,除了在电视中流传的包青天,人们还记得什么?哦,还有开封最骄傲的繁荣——《清明上河图》。在余秋雨的笔下,开封是一个褪了色的遗址。但是遗址中有最高大、最坚牢的构建古塔,还有荒草间的石阶。他对开封的领教是“爬塔是一种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千年前建塔的祖先们,不经意地留下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来俯瞰一代代的子孙是否有点出息、有点能耐。”
最后一笔升华:“是的,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构建,才有能力召唤后代。”十九世纪,俯视中国最高的构建大概是在上海外滩的国际饭店,百年后被东方明珠塔远远抛在后面。如今接二连三地被其它的高层构建所超越。不知秋雨是否爬过?
地处西北高原的兰州,能给余秋雨带来什么不同和惊喜呢?这里没有古城文化的沉淀,也没有现代文明的惊讶,它实实在在的地方是美食:牛肉面与白兰瓜,借此传递古城的两种风韵:浓厚与清甜。

文中也提到人,一位从牛肉面里带出来侠义之士,面铺掌勺的马师傅。但是,读者很难从他身上联想到兰州的历史经络、文化血肉,甚至美食味道。
我虽然没有去过兰州,但是我觉得作者似乎没有深入地领略兰州,或者没有打算过。否则不会没有兰州的历史、文化和“苦旅”的升华,而轻轻地捧上牛肉面与白兰瓜。最后,也只是感慨:“中华民族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可见体力毕竟还算旺盛的。有一个兰州在那里驻节,我们在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不知读者可曾细嚼结尾语中“毕竟”、“还算”和“无奈”,连“自豪”也仅仅“浮起一丝”的味道?
稍稍搜索一下,读者就会发现:
地理上,兰州地理位置处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交汇处,南北两侧为祁连山余脉。自汉至唐,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出现了丝绸西去、天马东来的盛况,兰州逐渐成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镇,是汉族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要枢纽。
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兰州一带属陇西郡地,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曾在此设令居塞驻军。
说到人,这位霍去病征讨匈奴,战功卓著。为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匈奴为此悲歌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近代史抗日战争中,西部回族将领在兰州率领马家军抵抗,使得日本侵略军直至战败未能攻克兰州城。这个奇迹,我是第一次听到。马家军,如此厉害!也就是这个马家军,曾经将红军西路军主力在祁连山附近击溃,给红军作战史留下耻辱的一笔。
以致于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这一点常常令我忿忿不平。还在五十年代时,少儿时读“红旗飘飘”这部回忆录性质的系列书,就看到西路军这段历史,曾经,甚至至今,为“英勇”红军的“悲惨”遭遇呜喑不止。
直到1949年,那位“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率军发起兰州战役。此时的解放军势不可挡,所向披靡,跟当日的红军天壤之别,重创守兵马家军,解放兰州。
要说风景名胜,兰州有古遗址50处、古城12处、古建筑15余处。走上一两处,或许亦可与开封古塔比肩。
随便掉掉书袋,就稀里哗啦掉下一堆跟兰州有关的历史和文化,还有红军的一段“苦旅”。但都不入作者的法眼。自然,读者也不能期待从文字和情感中升华出“一丝”什么感悟来。

不过,如果到兰州,还是要品尝一下牛肉面和白兰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