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似乎已经可以触摸到圣诞的气息。
早上出门,阳光开始耀眼。是否要戴墨镜?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了轻装。还没有走到一半,阳光不知什么时候就没有了。走到大门后往回返,开始觉得身上一阵阵凉意,没有风。抬头,没有阳光的一片灰白色,透明得连天上的云也没有了。四顾,房屋树下没有一丝阴影,远处也没有迷蒙得雾气。阴天了,一种没有阳光的透明,说不出来哪里有一种奇怪的魔幻感觉。
晚间,风大了起来。白天那些在风中乱舞的风向标,还可以看到风向标上那些彩色树叶在风中飞舞的五颜六色。夜里一阵风过来,风向标的树叶在激素飞旋中,化为透明,化为无形。要降温的预兆。
一岁平安又冬至 南国熏暖无寒意
明日冬至(21日23时59分)。《脸书》寄来5年前的一首习作小词《渔家傲》,题目就是“冬至”。5年前的冬至跟今年一天之差,然而,景色却大不相同,心情也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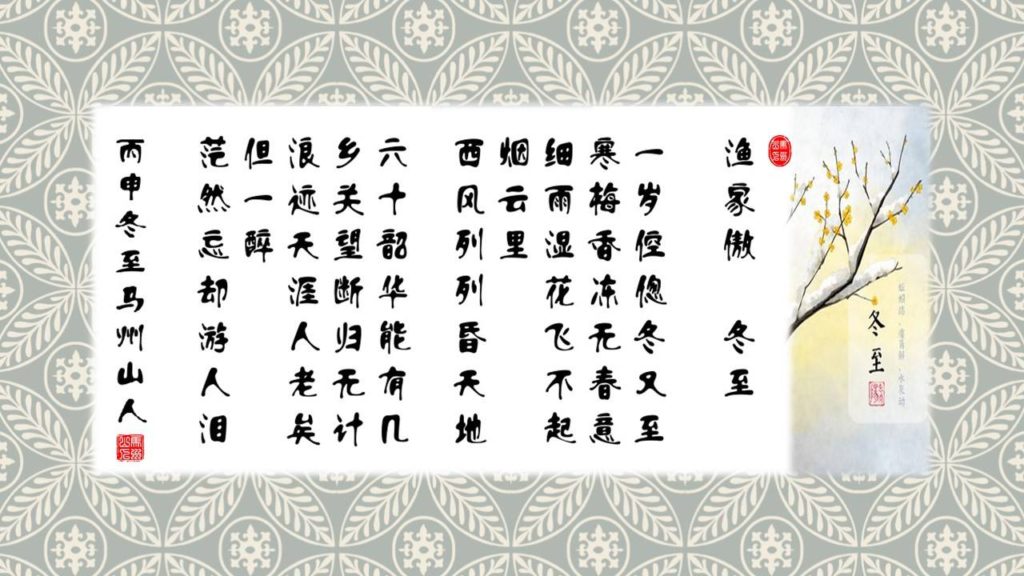
冬至即将到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吃食?而在中国各地传统习俗大不同。据说北方大多吃“馄饨”,代表冬至为“天地混沌”之始,当然也有吃饺子的,如东北地区。而南方尤其江南地区则普遍吃汤圆,意寓“团圆”。上海人在这个时节不仅吃汤圆,也吃甜白酒、花糕、八宝粥等,尤其新蒸的花糕是必不可少的食物,花糕以米粉、豆粉等为原料,发酵,更点缀以枣、栗、杏仁等果干、加糖蒸制而成。
不过,我小的时候,湖北好像冬至这天并没有什么特殊,不像端午节、中秋节以及元旦春节那样,在吃食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不过,现在应该不同了,是个节气似乎都要过得跟平常不同。这不,看到湖北宜昌一位同学的微信,说是“今天冬至了,提醒您冬至吃饺子!”而且还细分为:
吃韭菜馅(久财) 吃白菜馅(百财) 吃芹菜馅(勤财) 吃酸菜馅(拴财) 吃三鲜馅(合财) 吃荠菜馅(集财) 剩饺子溜热吃(留财) 剩饺子煎着吃(捡财)
听台湾朋友说,冬至大家第一件事也是要吃“汤圆”,还要祭祖。送来的照片汤圆上也满满是祝福——快乐!富足!和谐!感恩!平安!幸福!健康!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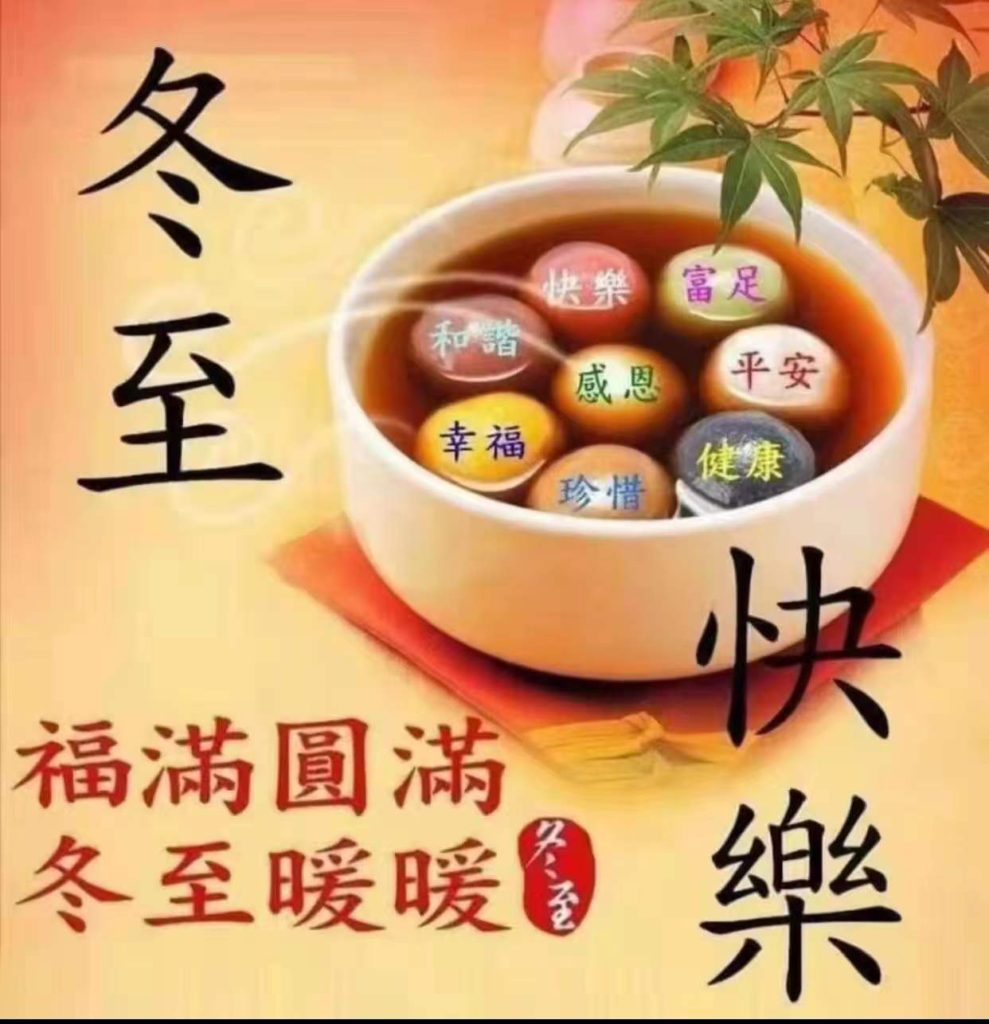
明天,中午吃冬至饺子,晚上吃冬至汤圆。我来个冬至南北通吃!
奥秘克隆新变种 新年圣诞阴影寒
随着冬至的来临,新冠病毒变种奥秘克隆(Omicron)在美国也越来越严重。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20日表示,高度变种的Omicron已在全美各地被检测到,而且已经超越Delta病毒株,在截至18日的当周,估计73%确诊案例是感染Omicron。并且,在美国许多地区,Omicron在染疫者的占比更超过90%。专家们说,他们相信真正的比率更高。
奥秘克隆整体流行率出现惊人窜升,凸显这种快速传播的病毒株可能产生一波新感染、导致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照护量能吃紧的疑虑。虽然有证据显示奥秘克隆所导致的重症程度低于Delta病毒株,但感染率激增仍可能让医院人满为患。
德州卫生官员表示,已出现首例与奥秘克隆病毒株相关的死亡案例。看样子,奥秘克隆将给今年的圣诞何新年节日带来阴影。
怎么办?美国正敦促符合资格的人士尽速接种追加剂以抵御Omicron。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都一直在为接种追加剂背书。
CNN报导,当节目主持人问特朗普“你接种加强疫苗了吗?”,特朗普回答“是的”。在后来发布的另一段较长的影片中,特朗普告诉支持者“我们做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们拯救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我们一起、我们所有人,不是只有我”。特朗普还继续说“如果没有开发出疫苗,新冠肺炎将对这个国家造成远远超出现在的破坏”。
不过,此刻他这种表态却难以被人们接受,尤其引起了他支持者的反对。当时台下观众就开始出现嘘声说,让特朗普忍不住对台下表示“不不不”,似乎试图平息嘘声。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特朗普的表态是对美国人民的负责,更是对他的支持者们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