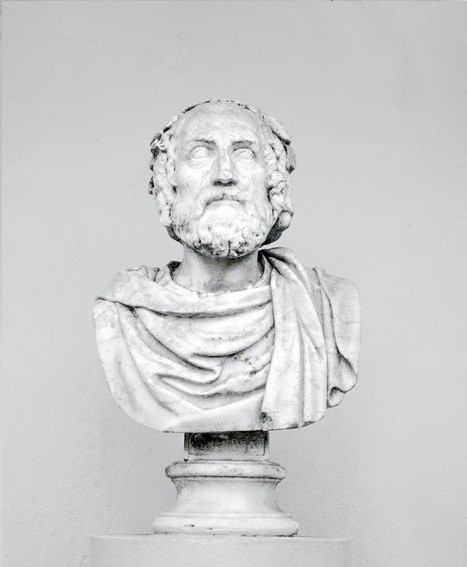现在读书,整个的感觉是速度减慢了。
一个是年龄的原因,体力不再如青年般的充沛。那时候一本长篇小说,都是一口气读完。一般都是一天就囫囵吞枣地看完。有时候会看到很晚,直至深夜人静,甚至看到天明。合上书,揉揉双眼,然后,长长地出上一口气。那气中有阅读后的疲倦,有被情节深缠的迷惘,有为人物深深地感叹,有被作者启发出的幽幽感悟,间杂着黎明将近的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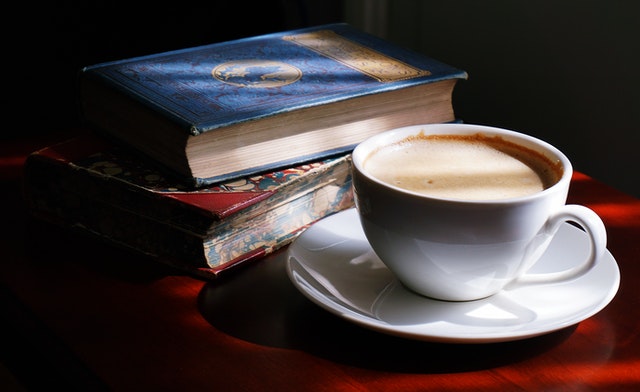
另一个原因,现在的读书,不再仅仅至陷入故事情节,而是有时会跳出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布局和叙述的技巧,揣摩作者的立意。就如现在看电视剧,陈旧的套路太多,一看就能猜出剧情发展甚至演员的表情和反应。猜中后,常常自诩为“三导”,就是导演和副导演之后的第三导演。当然,这种边看加上边想的双轨运动,显然就比一口气看下去要慢多了。现在,即使一本不厚的书,也要看上好几天。
再者,能看到的好书也多了。常常沙发边上摊上几本,床头上堆上几本,书桌上也有几本,还有电脑中亚马逊电子书阅读器(Amazon Kindle),那里有厚厚的中外文学大师经典,以及网络书站无数作品。不像以前书少,有机会抓住一本,就急匆匆地读完,看完了还要还给人家。现在的感觉,“我生有涯而书海无涯”。有些书拿起来就放不下;有的看到一半被打断了,就静静地等在那里;还有些徒有其表或者不对味口的书,打开了,又关上,一根书签插在那里,不知道何时还会再光顾。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读书也开始讲缘分了。
读书的步伐慢了,似乎跟作者更近了。

世代离家漂泊者 故乡原本是异乡
《文化苦旅》今日终于看完。作者的脚步最后走向海外,走向南洋,最后停驻在新加坡。讲到南洋华人,虽处太平洋,但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共同点,即使在大西洋岸边的我们,也深有体会。
从《华语情结》想到我们在海外筹办中文学校,就是努力为中文安排一个底座。让“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不过,我们这一代人过后,虽然第二代可能受到父母的影响,不会完全忘掉中文,但是,已经不能得心应手了。至于第三代以及他们的后代还会使用吗?我不知道。
新加坡的例子比较特殊。华人的后代已经中文拗口,英语顺溜。如余文所言:“逐渐抹去与故乡有关的种种分野,抹去家族的颠沛、时间的辛酸,就像从一条浑浊的历史河道上潜泳过来,终于爬上了一块白沙滩,耸身一抖,抖去了浑身浑浊的水滴,松松爽爽地走向了现代。不知抖到第几次,纔抖掉了华语,然后再一用力,抖掉了姓氏,只好让宗乡会馆门庭冷落了,白沙滩上走着的正是黄皮肤黑眼珠的杰克逊和麦克斯韦尔。”
在海外,没有了中文作为语言的载体,我们的根是否就会消亡?
最后一篇文章《这里真安静》,讲的是位于新加坡的一个日本坟地的故事,一个“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坟地。“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沈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
文章的地点和内容,除了跟旅行有关,似乎跟中国文化的关联不大,不知道该文为什么收到专讲中国文化的集子中来。
傍晚时分,有些疲倦,坐在后院乘凉。此刻室内外的温度相差无几,正是能在室外小息而没有夏日暑热的好时光。湖面上的夕阳闪烁,是玻璃门窗的反光照成,此刻正在慢慢地暗淡下去。双眼不觉有些沉重,渐渐迷糊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睁眼时,对面一轮明月已经升了起来。天色淡蓝,初升的月亮为深黄色,几近全圆。查看日历,原来是农历十五。

晚间散步,月亮已经升到头顶,亮得有些耀眼。清冷的安静中,社区渐入梦乡。走在小路上,还在想着书中的话:“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又何尝不是我们后代的故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