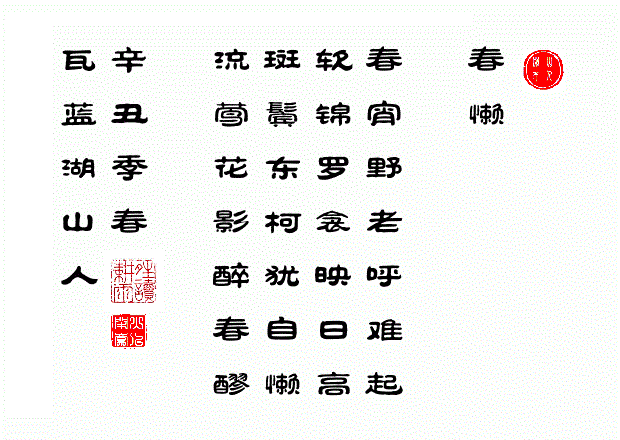继续阴天,温度开始升高。预报今日有雨,结果没下。这种不准确的预报很少见。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总是那么渺小。
达赖喇嘛打疫苗 不独不分谈西藏
印度近来单日确诊病例飙升,一跃超过巴西成为感染人数最多的第二大国。同时,目前印度的接种疫苗工作,已经进入的第二阶段,主要针对60岁以上的民众以及45岁以上的慢性疾病患者。
居住印度,现年85岁的达赖喇嘛,据报导,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一间医院,接种英国牛津大学及阿斯利康共同研发、由印度生产的AZ疫苗。施打完后他在现场停留半小时观察情况后离开。与他同住的10人也施打了新冠疫苗。

达赖喇嘛在脸书公开自己接受新冠疫苗施打的画面,他还呼吁民众打疫苗,“为了预防严重的疫情,接种疫苗非常有帮助”。
看着达赖喇嘛,不禁想起在印度北部,郁郁葱葱的松柏和终年冰封的雪山环抱中,那个喜马拉雅山麓小镇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和他所谓的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在这里已经度过了一个甲子的春秋。这一个甲子,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藏也是如此。
若是从1940年举行坐床典礼,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算起来,那就是80多年了。其间经历了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平叛后的流亡,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直到2011年,宣布卸下政治职务退休,结束达赖喇嘛长期的政教合一传统。人生可以经历几个“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但是,人生能有几个80年呢?
在我的印象中,达赖喇嘛一直是藏独的精神领袖。记得在大华府居住时,节假日受邀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加一些活动。通常,使馆大门外可以看到法轮大法的抗议。此外,有时候也会看到几个自称为“雪狮”的藏独分子在摇旗擂鼓呐喊。在美国,人们可以多方位地了解一些人和事物,从北京的角度或者华盛顿的立场,比如达赖喇嘛其人。中美建交后,达赖喇嘛曾经与中国有多次谈判,均无结果。近来,却发现他政治理念又逐渐变化,开始放弃独立,转向推动西藏自治的”中间道路“。
看到一些近期的报导,达赖喇嘛4月12日在与12位年轻人进行视像交互时,提到过去与中国政府沟通的细节。尤其回忆过去1954年,他见过毛泽东,也遇到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我那时对他们的行为感到非常振奋,而且我甚至提出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想法。”达赖喇嘛解释,那时候会有振奋的感觉,是因为“深深地感觉到当时共产党的精神,的确是为广大劳动人民福祉而着想的,这种为广大劳动人民着想的理念,跟我推动70亿人皆是一体的理想基本上是雷同的。”
达赖喇嘛提到的“全世界70亿人是一家”的理想,大概源于佛教普渡众生的概念。他的普渡,从西藏一隅,到中华大地,继而印度,最后到全世界。在2019年一次访谈中,他回答说:“从有形层面上说,西藏是我的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的家。因为我们不追求独立和分裂。”听到达赖喇嘛这一十分明确的回答,令我十分吃惊。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颇有些像当年中美建交时,基辛格提到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这一概念。既承认一个中国,又承认台湾或者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了这个大前提,具体的问题应该都好谈。
“但是精神上,印度是我们的家。因为西藏的佛法、佛教的传统是由那烂陀寺的伟大的学者传来的。”有形层面上的家在西藏,在中国。精神层面上的家,在印度,在佛教诞生的地方。作为一个佛教徒,有宗教信仰的人,这样讲自有其道理,也无可非议。
回到4月12日的访问,达赖喇嘛重申,他所寻求的并不是西藏独立,而是藏族愿意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里。所谓“共和”是“一起合作”、“联盟”的意思,所以我们想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联邦的体制里。达赖喇嘛称,藏族不希望受到极权体制的掌控,“因为这个本身是会有问题的,而且中国人民自己本身也想要更多的自由。我们要的是中间道路。”
记得1980年代,邓小平在世时,曾表示达赖喇嘛可以返回中国,但“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如果当时达赖喇嘛接受这一要求,可能他现在已经在拉萨了。听说,他当时有一个就未来西藏地位问题提出“五点和平计划”,并且派遣特使与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可惜,中国那时没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美国也没有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最终,双方没有对那个“中间道路”达成一致看法。
时间在变化,形势在变化。中国已经从建国初期1950年代的百业待兴,发展到如今2020年代的繁荣昌盛。人也在变化,达赖喇嘛从开始的坚持藏独演变到现在的放弃藏独。不过,晚变不如早变,历史的机遇一旦错过,就再也不会发生。有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讲到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进入21世纪后,西藏又发生了一些骚乱活动,形势和结果就发生了变化。如果当年早一点改变,达赖喇嘛此刻说不定在北京,而不是在华盛顿接受采访了。

相对于疆独要求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武装暴乱,达赖喇嘛的和平抗争方式,跟美国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民权运动相似,是得到世界大多数人赞同的。那么,达赖喇嘛现在的“中间道路”又是什么呢?
达赖喇嘛的下面一段话挺有意思:“我们相信生生世世,所以,我们的家可以在这里,也可能在别的星系。我们并不把今世的家看得非常重要。”对于世界各地的难民来说,“不管身在何处,都应该这样看:我们是同样的人。如果一味地想,我们是难民,跟当地人不一样,就很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挫折感。说到底,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家,70亿人都是兄弟姐妹。不论你走到哪里,都是人的家,人类的家。在精神上,你就不会觉得孤单,这一点很重要。今天世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我们’和‘他们’。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他提出“必须努力创造一个70亿人的共同体。”听起来,跟中国太平天国讲的世界大同,和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理想和出世是丰满的,现实和入世是骨感的。达赖喇的远大理想和近期目标“中间道路”还是没有实现,他老人家今天还是呆在小镇达兰萨拉,过着寄人篱下的难民生活。
就在今年的4月中旬,流亡国外的藏人进行投票,选举下一届流亡政府司政和议会议员。由于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这次选出新的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议会,将对流亡藏人的未来影响很大。作为达赖喇嘛提出的西藏政治解决方案“中间道路”未来走向,受到多数流亡藏人的关注。也受到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关注。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西藏流亡政府高层官员说,所谓的“中间道路”,是在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西藏人既不接受西藏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位或状态,也不寻求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而是取中间路线,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架构范围内寻求整个西藏三区施行名副其实的自主自治,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西藏问题。
如果要改变“中间道路”,根据西藏流亡议会制定的宪法,必须经西藏流亡议会决议才可改变政策,但在“中间道路”之下,仍有许多空间可以根据新司政的想法进行调整,选出的新司政,将会在“中间道路”的架构之下,根据实际状况做出对藏人最好的选择。
从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近来的讲话看,感觉他还是希望有生之年回到西藏的。只要不搞西藏独立和分裂,如达赖喇嘛所言,中国还是会欢迎他回到拉萨的布达拉宫的。但是,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如何把他的“中间道路”变为北京可以接受的“可行道路”,这是需要大智慧的。我们不仅将拭目以待,更希望看到,就像当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全部东归一样,达赖喇嘛能在有生之年率领在外流亡藏人,一起回归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