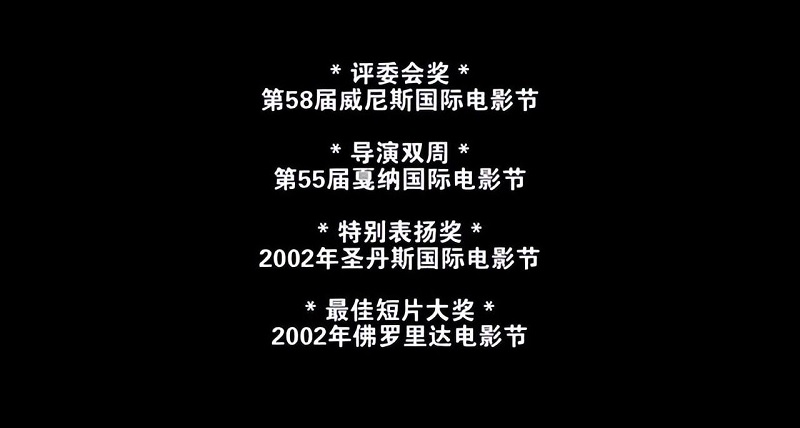今天到我们坦帕的火车站,去接从纽约下来的女儿一家。来到坦帕第六个年头了,到飞机场去过无数次,到坦帕的火车站还是第一次。
坦帕火车站算得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火车站,于1912年启用,比武汉的老汉口火车站(大直门)晚十年左右,至今页走入100多年的岁月了。

坦帕火车站最初目的是将大西洋海岸线、海滨航空线和坦帕北部铁路的客运业务合并在一个站点,车站位于北内布拉斯加大道601号。从我们家开车到火车站,大约三十来分钟。不过开到火车站,看到了火车站红色的建筑,就是找不到如何进入停车场,硬是在周围饶了两个圈子,才找到入口。
火车站的全称为坦帕联合车站 (Tampa Union Station,简称TUS)。美国很多地方的火车站都叫“联合车站”,我们当年住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就住在“华盛顿联合车站”附近。不过华府的联合车站比坦帕的要漂亮得多,除了火车运输以外,还有兼有商业、饮食和观光的功能,站在车站的大厅里,完全感觉不到这里是个火车站。
不过,小有小的好处。我进去的时候大约在12点半,女儿的车次是银星号(Silver Star)91次车,下午1:09到达。车站里候车的人,寥寥无几,一眼就将火车站内尽收眼底。坦帕联合车站前面一共两个大门,进入后一个大厅,一边两排候车的长椅,上面有十来个侯车的人。左手边是两个售票和行李窗口,买票的人少,后来干脆关了一个窗口。对面是两个出口,跟入口相对应,出去就通往站台。右边一厕,有个卫生间和贵宾候机室。没有火车站应有的嘈杂和喧嚣。
于是出来看看外观,一栋长方形的建筑,四面是那种老式的红砖墙。一看就是后来修复的。迎面四扇圆拱型的大玻璃窗,上面是一层白色的水泥面,通常有点气势的建筑,这里都会有雕像,或人或神,要不就是名人语录或神的旨意。但是这上面朴素的什么都没有,在上面又是红砖的顶。设计简单大方,没有什么花哨之处。

火车站旁矗立一座时钟,大概是早期的一个计时器,下面的石柱刻有许多图案,类似天安门前的华表。不像老汉口火车站,火车站迎面大门楼正中就是一个口大钟,还鸣钟报时。从火车站外面看,笔直的铁轨和站台伸向远方,站台上清净得一个人影都没有。记得儿时乘坐中国的京广线,火车一到站,站台上满是卖东西的,地方小吃、大众点心、馒头、油饼、鸡蛋、烧鸡,一时间热闹极了。
据介绍,80年代的坦帕火车站的状况严重恶化,于1984年关闭。车站关闭后,乘客使用了位于车站站台附近的临时预制车站大楼。一晃十几年后,于1998年修复并向公众重新开放。如今,它作为“美铁”银星线车站运营,往南前往迈阿密或往北开往纽约。
来坦帕后,听说坦帕火车除了载客,还可以载客人的汽车。客人可以将自己私车开到车站,连人带车一起坐到其它地方,比如可以坐到华盛顿附近的北维州,下火车后,汽车也跟着下来,可以自己开车在华府旅游。
“美铁”(Amtrak)在其2022 年报告中称,该车站是美铁在佛罗里达州第二繁忙的车站,车站乘客量为11万多人次。看到这里,想想中国春节多少亿人乘火车回家过年,一个武汉的客流量,一天都超过这个数。不过,我还是喜欢坦帕这样的小车站,安静、干净、轻轻松松不慌不忙地上下车。谁愿意像个沙丁鱼一样被人潮挤上火车,压缩饼干一样挤在车厢里,不禁想起大串联时,从车窗里爬上车,睡在行李架上和座椅下面,以及闷罐子车的经历。
80年代,坦帕火车站的状况严重恶化,于1984年关闭。车站关闭后,乘客使用了位于车站站台附近的临时预制车站大楼。一晃十几年后,于1998年修复并向公众重新开放。如今,它作为“美铁”银星线车站运营,前往迈阿密或纽约。
坦帕市官方桂冠诗人老詹姆斯·托克利(James E. Tokley Sr),于2009年创作了一首诗《坦帕联合车站史诗》,纪念坦帕联合车站的历史。摘录其中描绘火车站的部分。
(外面的建筑)
对于一万三千四百平方英尺的面积
红砖通勤列车大厦,
白色花岗岩柱和倾斜的屋顶
就像遥远罗马的帕台农神庙屋顶!……
——这个比喻有点过了,也许以前有过辉煌,现在可看不出帕台农神庙屋顶富人影子。去年我刚从希腊雅典参观过帕台农神庙归来。
(里面的装潢)
这些华丽的阳台,宽敞而坚固
这些拱形天花板,巨大的绿色门,
华丽的水磨石地板
并设置天窗来柔化阴暗……
——我看到的是室内墙角上面油漆经久不维修的剥落。
(萧条的日子)
至于我们曾经认识的车站,
这里成了鸽子飞翔的地方
并安全地坐落在看不见的地方,
为了躲避掠夺的鹰,在夜间。
但车站空荡荡、起泡的墙壁 ……
(今后的期望)
那么,站长,请再一次,
打开车站的绿色大门
让阳光和乘客进来
铁马时代再次来临!
听到这个声音我们会兴奋不已
银色流星降临
站长唱歌时的轨道
“你的火车到了!
把你的东西都拿走!” ……
12点55分,火车到站了。女儿、外孙女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到了。

往时今日
六年前,习作【如梦令·戊戌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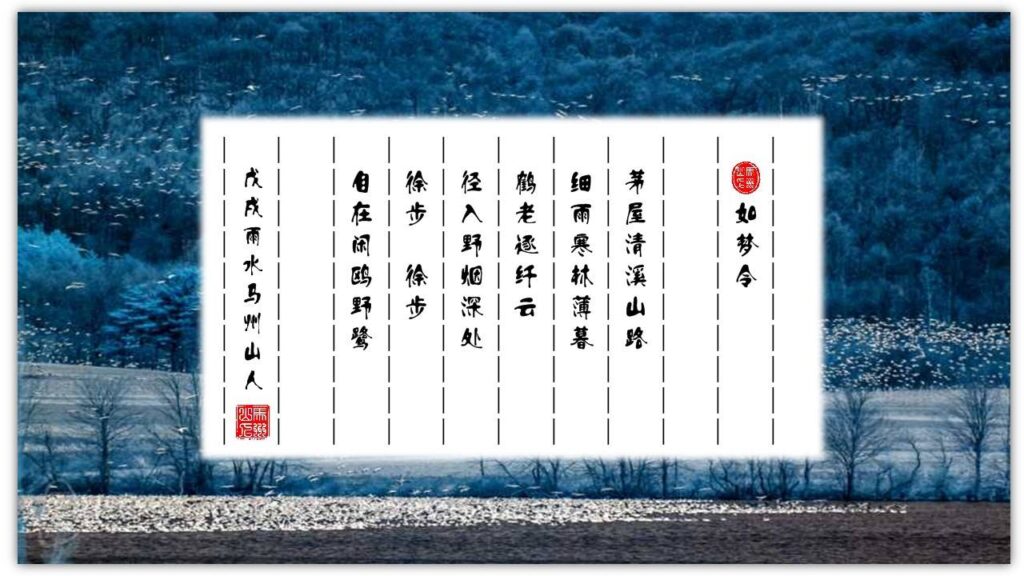
茅屋清溪山路
细雨寒林薄暮
鹤老逐纤云
径入野烟深处
徐步
徐步
自在闲鸥野鹭
02/19/2024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