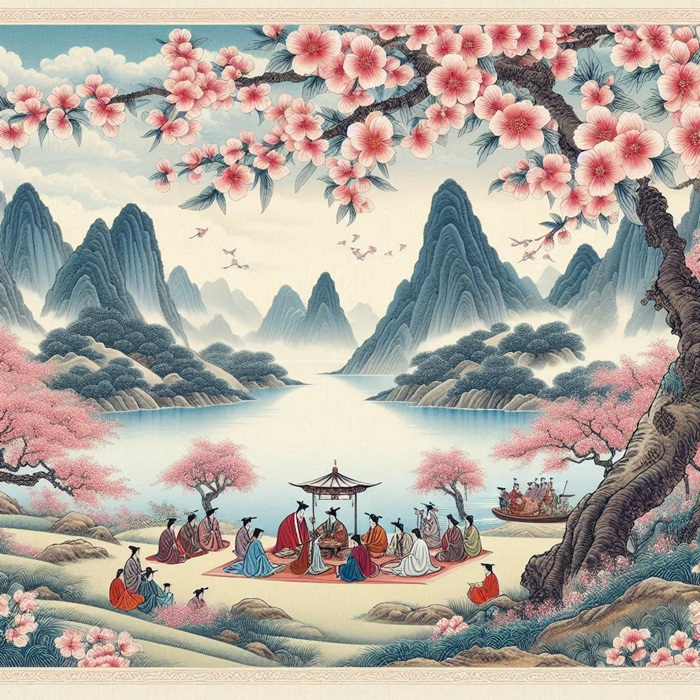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粘泥的雨鞋是我同伴
雨衣闷出大汗在胸膛
黑夜的大雨是打湿的衣裳
拿把电筒在手上
噼啪的雨声在流淌
滴答滴答滴答它们唱
还有一支水流在雨鞋里响
雨水下在脸上
哼一曲上班小调
任烦恼在夜雨中飞扬
多少落寞惆怅
都随回城飘散
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
这是当年在地质队符嘉诗改编的歌。
几乎每个雨夜,符嘉诗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多年前在地质队的那段时光。他站在窗前,看着雨滴打在玻璃上,仿佛回到了那个寒冷的夜晚,和那些同样在风雨中坚守岗位的伙伴们一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50年前,符嘉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地质队工作。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好奇,他踏上了这段全新的旅程。地质队的日子充满了挑战,野外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压力让他感到无比疲惫。
符嘉诗的手指停在工作日志本上褐黄的字迹间,“1975年12月15日,夜班,雨…”
那年的冬天显得非常寒冷,连绵不断的阴雨让大地变得泥泞不堪。一个夜晚,他被安排上大夜班,时间从晚上11点到早晨7点。身穿雨衣,脚踏雨靴,手拿电筒,符嘉诗在雨夜中独自走向钻井平台。脚下的田埂被雨水浸透,泥泞的路让每一步都变得沉重。
雨水顺着雨衣的下摆不断流进他的雨靴,内衣也湿透了。湿冷的感觉从脚底渐渐蔓延到全身,他感觉每一步都像是在泥泞中跋涉。他不禁想起,在城里柏油路上的逛街,校园田径场上的晨跑,和林荫树下人行道的闲庭信步。那种从容变成此刻泥泞路滑带来的紧张,那种悠闲化为雨水汗水带来的潮湿和不舒适。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城里呢?
等到了工地,他拔出陷在泥里的雨靴时,月光突然刺破云层。靴筒里晃动的积水,竟盛着整片摇碎的夜空。
此刻,脚下书房地板平坦的木纹与当年田埂上的泥痕走向一致,符嘉诗总是不自觉沿着某种路径踱步,仿佛回到当年的田埂路上。
在钻井平台上值班,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城市生活的怀念。雨水顺着雨衣流进雨靴,裤子湿透了,脚底的冷水让他感觉到刺骨的寒冷。宵夜时分,大家围坐在火炉旁,把馒头和红薯放在炉子底部烤,浓浓的香味夹杂着些许泥土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驱散了寒冷和疲惫。火炉边的温暖和同事们的关心让他感到艰苦环境下的一丝温馨。
符嘉诗的手指抚过工作日志本上的油渍,那些被老王戏称为”防伪标记”的印痕依然清晰。翻到折角的那页,钢笔墨水早已褪成秋叶般的褐黄:
日期: 1975.12.15 19:00
坐标:东经112°46′ 北纬28°12′
天气符号:🌧️🌀(降雨量22mm,风速5级)
工作:ZK-07孔 进尺286m(遇灰岩破碎带)
备注:第3次更换钻头。*老陈的姜茶配方升级(新增橘皮),建议载入队史。
那年事故中崩飞的齿轮,已经成为此刻书桌上的镇纸。书房灯光下,那个当镇纸用的锈蚀齿轮压着信纸。沉香线香升起的烟柱里,似乎混进了记忆中的烤红薯焦香。灯光透过齿轮凹痕,墙面的投影开始缓慢旋转。当影子转到1975年井架的角度,隔壁似乎传来钻机启动的震动波。
正当符嘉诗和同事们在火炉旁休息时,钻井平台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钻机停了下来。符嘉诗和队友们立即冲向平台,钻机卡住了。一个崩飞的齿轮,飞到钻井平台的一角。好险,没有伤到人。井内压力骤增。在这紧张的时刻,大家迅速冷静下来,要知道,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拉开钻机电闸!”班长老王的吼声撕开雨幕,“保持立管压力不超过红线!”
那些红线是大地血管,我们的脉搏在其中共振!——多年后的的今天,符嘉诗仍然忍不住情绪的激动。
符嘉诗扑向液压控制器,手套上的油污在仪表盘划出闪电状轨迹。他压下操纵杆的动作,像在折叠四十年的时光。液压管嘶鸣着与此刻的雨夜铆合。
队友们分工合作,发现问题,然后加紧疏散压力,直到钻机恢复正常运转。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符嘉诗和队友们都松了一口气,汗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仿佛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还记得,钻杆卡死的瞬间,小周工具箱里掉出他未婚妻的照片,头上那个红发卡好不耀眼。原来我们拼命守护的不仅是地底岩层,更是所有等待的眼睛。
眼睛里闪现出一个镜头:一个戴红发卡的姑娘举起岩芯样本:“符老师,我是周晓雨,ZK-07孔现在由我负责。”
工作日志边缘添着新的铅笔批注:“上周同学会见到周工(当年的小周)孙女,她戴着当年照片里的同款红发卡。我们守护的眼睛,终于看到了我们没见过的星辰。”

合上工作日志的刹那,晨光正掠过齿轮镇纸的凹痕。那些被岁月磨平的齿尖,在光线下投射出当年井架的轮廓、雨夜中的坚守、乡间泥泞的小路、钻井平台的火炉,还有那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的旋律,仿佛正从地底的岩浆中传来。
02/28/2025 初稿于瓦蓝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