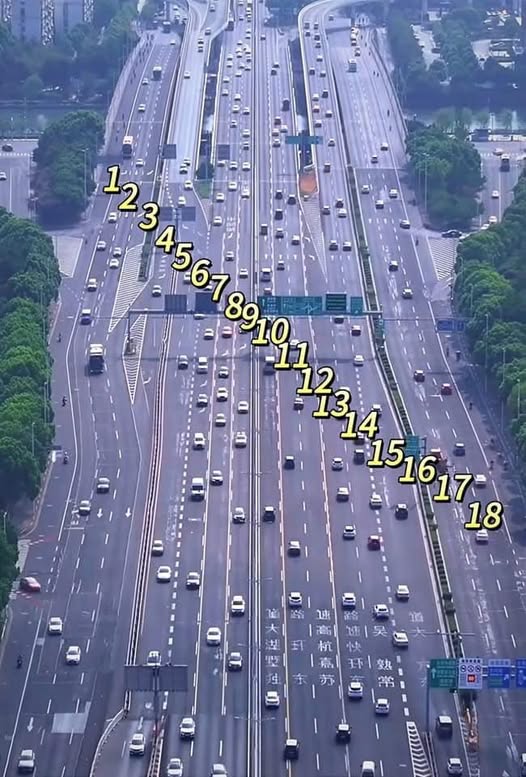“Blackbird singing in the dead of night,
Take these broken wings and learn to fly.”
—— The Beatles, “Blackbird”
“黑鸟在死寂的夜里歌唱,
带着这些破碎的翅膀,学会飞翔。”
—— 披头士乐队,《黑鸟》

比尔28岁,一个美国德州的大男孩,来到意大利罗马学习意大利语。
他的帆布背包里总塞着一本《披头士歌词集》,在《黑鸟》的页面边缘,铅笔批注密密麻麻:”破碎的翅膀是自由的切口””所有未唱完的音符都会变成羽毛”。每当罗马的喧嚣让他窒息,他就躲进街角咖啡馆,用走调的嗓音哼唱:”黑鸟在死寂的夜中飞,你只等这一刻展翅高飞……”
罗马的喧嚣,街头橄榄摊的酸涩味混着汽车尾气,让他倍感压抑。而意大利语的学习也如同蜗牛般缓慢。过往家庭的纠葛与生活的失意将他压得透不过气,每逢周末,他便逃往城外山上的修道院,躲避城市的喧闹。他开始思索,是否要将一生奉献给信仰,成为修士。两个月后,他在修道院开始了沉默的净修。
修道院静修的第二个月,比尔开始刻意按照院长嬷嬷的教诲生活。他学着沉默静修,把每天的忏悔写进《圣经》边缘的空白处——”愿主宽恕迷途者”。他甚至开始相信,或许痛苦真的可以通过信仰被冲刷掉。
他试着在晨祷时跟随合唱,低声念诵《圣经》,但每当“主啊,宽恕迷途者”出口,脑海里总浮现父亲醉酒挥舞酒瓶的影子,音符如碎玻璃般刺耳。
他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他仍然无法在清晨的圣歌里感受到平静。午夜梦回时,母亲倒下时的尖叫声依旧在石壁间回响。
这天夜里,他在修道院的回廊散步,经过圣器室时,注意到墙角的一个古旧杯子,上面有一道极浅的裂痕。他犹豫了一下,伸手去碰,杯子在指尖轻轻震动,冰冷的瓷面传来一阵微不可察的嗡鸣,像黑鸟翅膀的低语。
第二天,他向修道院图书馆的修士询问,”如果圣器破损了,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
修士抬起头,淡淡地回答:”所有圣器都会有裂痕,只是有些裂痕藏得比其他的更深。”
那一刻,比尔愣住了。
这句话在他心里掀起了什么,他还说不清。但他知道,自己又开始做梦了——梦见那些破碎的酒瓶,梦见母亲的泪水,梦见一只黑鸟拍打着翅膀,却怎么也飞不出囚笼。
“咚!”
陶瓷碎裂的尖锐声划破修道院的寂静,像一道裂缝刺入比尔的耳膜。他冲进厨房,一股橄榄的酸涩味扑面而来——南希修女踮脚擦拭彩窗,橄榄腌罐在她脚边炸开,紫黑色的汁液漫过青砖缝,像一条蜿蜒的蛇,浸湿了石壁上斑驳的苔藓。
“需要帮忙吗?”比尔弯腰捡起碎片,指尖触到冰冷的瓷片,脑海闪过父亲醉酒砸碎威士忌瓶的画面——那是十四岁生日,母亲的尖叫与玻璃碎裂声交织。
“别动!”南希抓住他手腕,指甲短而粗糙,掌心有常年搓洗圣器留下的茧。
她的黑袍袖口散发出薄荷香,混着橄榄的酸涩,孔雀蓝腰带在阳光下闪着金光——那是她母亲留下的遗物,十五年前,她曾发誓用它系住信仰,却在孤独的夜里发现它更适合系在吉他上。
南希蹲下身,孔雀蓝腰带从黑袍下摆滑出,金线鸢尾在罗马盛夏的阳光里燃烧。
“您不觉得,”比尔盯着那道蓝光,”戒律就像这罐子?越是用力擦拭,越容易打碎。”
南希用抹布裹起碎片:”但神性往往藏在裂缝里。上周我打碎圣餐杯时,发现杯底刻着十五世纪修士的情诗。”她忽然压低声音,”要保密。”
以后,每周三午祷后的圣器清洗,成了他们心照不宣的仪式。
南希总爱谈论远东雨季:”加尔各答的苦修者说,湿气能让檀木念珠发芽。”
比尔则用结巴的意大利语描述德州沙漠:”夕阳会把仙人掌的影子拉长,像上帝在弹奏班卓琴。”
一个黄昏,南希掀开面粉袋,老式收音机正沙沙播放《黑鸟》。她跟着哼唱,手指在陶罐边缘敲出切分音。比尔发现她脖颈有块浅褐色胎记,随吞咽微微起伏,像沙漠里干涸的河床。
“试试这个。”南希往圣餐杯挤柠檬汁,”摇滚弥撒需要酸味伴奏。”
比尔抿了一口,五官皱成核桃:”你们修女都这么疯?”
“疯?”她晃着杯子,金箔在杯沿颤动,”黑鸟需要裂缝,修道院需要摇滚。这是基本常识。”
一天夜晚,比尔和南希坐在回廊的长椅上,修道院的长明灯在风里摇曳。比尔正翻看南希的《圣经》笔记,发现她的手写拉丁文在《雅歌》旁批注着奥维德的诗句——”爱是战争,和平的条约永不会在恋人之间签订。”
“你是怎么进修道院的?”他突然问道。
南希低头拨弄着腰带的金线,半晌才说:”矢车菊是我母亲最喜欢的花。”
比尔没听懂。
“十五年前,我还是个孩子,母亲带我去法国卢尔德朝圣。她得了绝症,觉得圣水能治愈她。”南希指尖在衣摆上轻轻擦拭,像在抹去什么看不见的痕迹,”她把我托付给修道院,说‘上帝会照顾你’,然后就走了。”
比尔屏住呼吸。”她是走了,还是——”
“她把自己沉进河里。”南希的声音很轻,”第二天,修女们为她做了弥撒,但没有人敢讨论她的死。他们只告诉我,她的灵魂已经被净化,而我,应该把自己也奉献给主。”
比尔嗓子发紧。他想起自己童年时,那些被威士忌砸碎的夜晚,自己也曾盼望着某种超脱,盼望着奇迹能修补破碎的家庭。
“你相信他们说的吗?”
南希抬头看着修道院彩窗上耶稣受难的画面,玻璃上的裂纹刚好从耶稣的心口延伸下来,像一道疤痕。
“我不知道。”她的语气第一次有了松动。”但我知道,所有沉入水中的人,都不会再浮上来。”她的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吞没,她的目光落在长明灯的火焰上,瞳孔里仿佛闪过河水的倒影。
在修道院后花园,南希倚靠在石雕圣母像下,目光落在比尔手中的烟卷上。
“你为什么不信神?”她问。
比尔弹了弹烟灰,语气淡然:“因为我信自由。”
南希低笑一声:“可自由是虚幻的,信仰才是指引。”
比尔扬起眉:“真的吗?如果信仰能指引你,为什么你还站在这里,和我谈论自由?”
她一怔。指尖下意识地揉搓着手腕的银十字架。
比尔盯着她,语气缓慢而锋利:“你不觉得,神要的不是信徒,而是囚徒吗?”
南希怔住,嘴唇微微颤抖,像是要反驳。但最终,她只是缓缓低下头,将十字架摘了下来,放在石雕圣母的脚边。
“……也许,你说得对。”她喃喃道,“我一直都在骗自己。”
院长嬷嬷的调令随着雨季降临。在挂满苦像的密室,枯槁的手指碾过南希的《圣经》笔记——在《雅歌》的空白处,她用拉丁文抄写着奥维德的句子:”爱是战争,和平的条约永不会在恋人之间签订。”
“十五年前你戴着矢车菊腰带入院时,我就知道你不是为上帝而来。”嬷嬷的念珠碾过书页,”下周去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修道院。那里的盐湖能结晶过热的灵魂。”但是,念珠在书页上停顿了一瞬,像是被雨夜的求救声打断。
记得那年,南希提着灯,站在修道院的大门前。门外,一名衣衫破烂的年轻女人跪在雨中,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求您……求您让我进来……神不会让我死在外面的,对吧?”她的声音在风雨中几乎被吞没。
南希的手指紧紧扣着门闩,心跳快得像是钟楼上急促的钟鸣。
身后,院长嬷嬷的声音冷静而坚定:“我们不能收留她。神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
南希回头,雨水顺着她的额角流下:“可她的孩子是无辜的……”
“神自有安排。”院长嬷嬷的目光沉静,如同教堂壁画上圣母慈悲而冰冷的眼神。
南希的手颤抖着,最终缓缓放开门闩。门缓缓合上,将雨夜与求救的声音隔绝在外。
但她的心,仿佛也被关进了另一座牢笼。

离别前夜,比尔用烛台砸碎彩窗。烛台砸下,彩窗爆裂。琉璃雨倾泻,南希在琉璃雨中弹唱《黑鸟》,血与橄榄油混在一起。
“跟我走。”比尔将歌词集塞进她行囊,”去埃及、西班牙,去所有裂缝足够大的地方。”
南希却撕下《黑鸟》歌词页,背面写满批注:”你看,我早把你的羽翼缝进祷词了。”——在麦卡特尼的手写谱旁,她翻译了阿西西圣方济各的诗句:”爱是焚尽枷锁的烈火,灰烬里会升起新的黑鸟。”
晨祷钟声响起时,南希将孔雀蓝腰带系在他腰间:”金线是用唱诗班蜡烛熏染的。现在它属于所有未起飞的黎明。”
多年后,比尔在德州沙漠开了间旧书店。某个黄昏,他翻开那本边缘卷曲的歌词集,发现《黑鸟》页夹着一根孔雀蓝丝线。窗外,一只黑鸟正撞击教堂彩窗,但它没有撞碎,而是穿透光影,飞向更远的天际。
黑鸟掠过彩窗,翅膀轻拍出“沙沙”的声响,光影在比尔脸上颤动,像是南希的笑声从远方传来。”所有裂缝都是候机室,我们终将在破碎处起飞。”
风翻动书页,暮色中,比尔指尖抚过那根孔雀蓝丝线,嘴角浮现一丝笑意。远处的沙漠风声中,他仿佛听见南希低唱的《黑鸟》,音符如裂缝中的光,指引着他。
他合上书,推开门,风裹挟着书页的余香,他迈步向前——某个未知的方向。
02/17/2025 初稿于瓦蓝湖畔
02/20/2025 再稿于瓦蓝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