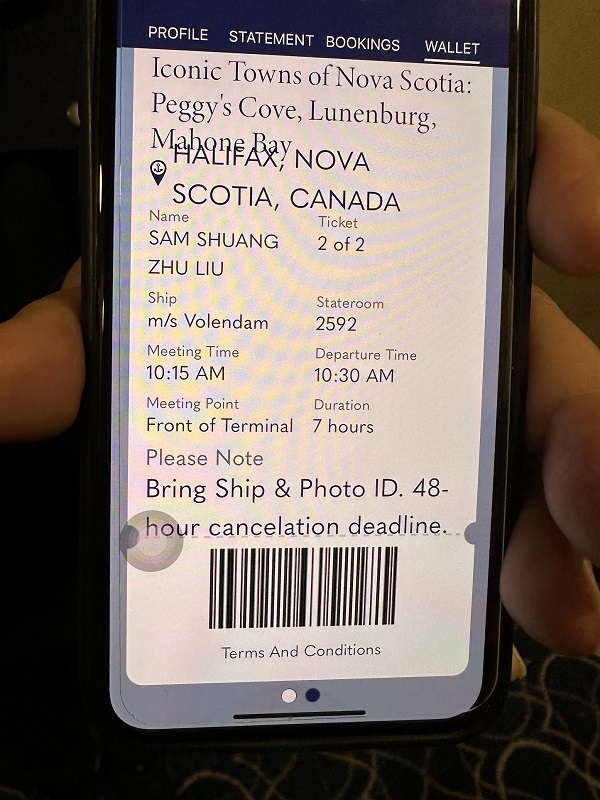悉尼 Sydney,新斯科舍省 Nova Scotia, 加拿大Canada
看到悉尼(Sydney)这个词,我的第一个反映是澳大利亚那个人口最多的城市,5000多万人,和那个世界著名的贝壳悉尼歌剧院。其实,我们的下一站悉尼,只是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一个小小的城市,人口仅3万余,同名而已。

悉尼位于新斯科舍省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的东海岸,1785年由英国人建立,正值大清朝盛世的乾隆,距今不过200多年的历史。
20世纪初,悉尼作为北美主要钢铁厂区之一,加拿大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曾经也有过自己的辉煌。那阵子,悉尼人口迅速膨胀,成为新斯科舍省的第三大城市。不过,20世纪70年代初后,由于工厂陆续断关闭,悉尼几乎沦为与美国中西部相似的铁锈地带。好在悉尼靠海,成功产业转型为客户支持呼叫中心和旅游业。
上午10点,游轮靠岸。正是北国春寒料峭时分。大晴天的太阳照着,风呼呼地吹到衣服里面,甲板上已经感到加拿大的寒意。于是穿了一件毛衣,外罩一件夹克衫,这是佛罗里达冬天最冷时刻的防寒服装了。不料,一下船,气温低,风大刺骨,毛衣加上夹克衫也抵挡不了冷风刺骨地往里钻。

一下船,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把巨大的小提琴树立在码头上,给悉尼标上了艺术和文化的标签。如果将10个中等身材(1.7米)的人摞起来,才跟这把小提琴一样高。看到介绍说,小提琴最早由苏格兰移民带到布雷顿角岛,流传至今,又融合了其他移民和当地原住民的元素,成为悉尼文化的一大特色。一个三万人的小镇,能拥有这么大一把小提琴,足以牛逼天下小提琴!
码头上有一个专门的游轮旅游服务中心,有两层楼高。楼下分两个大厅,一个为游客休息的地方,一个是供小贩们展示他们商品的商摊。商摊有当地特色的各种旅游纪念品,当然,也包括无所不在且价格便宜的中国义乌小商品。大厅中有一个灯塔状的售货亭,让我回想起昨日游览过的灯塔。

旅游中心里面很暖和,出来外面还是感到冷风飕飕。幸而离船不远,回去换了一件多年未穿过羽绒服。记得上次穿这件羽绒服,还是多年前深秋时节在彼得堡涅瓦河上泛舟。那都是退休前的事情了。

旅游服务中心外,有一系列展示当地历史和文化的棚板房。其中有一位老铁匠,正在火炉里锻打铁器。头戴早期英国绅士的黑色礼帽,如福尔摩斯探案的行头,棕栗色的长发从帽檐下经过肩膀流落的胸前,与满脸的大胡子混在一起。身著黑呢短大衣,胸前罩一件皮革工作罩裙,手持铁锤,正在铁砧上敲打一个通红的铁棍,活脱脱一幅十七八世纪欧洲工匠(Blacksmith)形象。我问他可否拍照,他于是摆了个竖起大拇指的POST。不管这是乾隆年间还是工业大革命时代的悉尼人,这都算是此行难得的历史一瞬存照。

树木光秃秃的,树枝在春风中瑟瑟发抖。一些勇敢小花在阳光中犹自开了。有人穿着皮夹克在椅子上晒太阳。阳光明媚,海风呼啸,冷风直往衣服里面灌。这就是4月底的悉尼景象。

走到码头出口处,看见一组雕像,一个壮汉身披一件风衣,一个孩子依偎在壮汉的身边。身后的石牌注解说明,这是纪念早期移民的雕像,并有一段对话,展示当年移民踏上这块荒芜贫瘠土地的艰难情景。
—— 老爸:“孩子,这日子再苦,没有主教和领主的压榨,只要有土地,就有希望。”
—— 孩子:“老爸,我信你。我不怕吃苦。我们一起干!”
这就是早期欧洲移民的向往和希望:只要没有压榨和剥削,只要有土地,日子再苦,我们都有希望。可惜,当时国人正处在大清乾隆盛世,谁又愿意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否者,这个雕像可能就是头上盘着大辫子的大清子民。

码头外面一片空地,像是个公园模样。远处又是一组群雕。走近前去,看到说明。这是一组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的水兵们在跟德军作战时,不幸被德军水雷击中,水兵们相互救援坚持战斗的情景。加拿大参加二战的这段历史我没有听说过,看到这组雕像,让我了解到,加拿大人在二战中,也加入了盟军反法西斯阵营,是出过力,打过仗,流过血的。
不知道他们生还了没有?想起一个镜头,北洋水师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被日本军舰击沉,全船官兵无一生还。自此一役,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一个曾经为先师的泱泱大国,就此背上耻辱的“东亚睡狮”的称号。历史告诉我们,人多,不管用;地大物博,不管用;船坚炮利,也不管用,银子多,更不管用。君不见,800万两北洋水师的银两,被用在为老佛爷祝寿的颐和园万寿山?看着这几尊雕像,面对大海蓝天,不禁让人沉思不语。

走到悉尼的大街上,虽然人口少,只有2-3万,但是城里也是有模有样的。有一些现代城市的高层建筑,有干净整齐的街道。有来来往往的车辆,只是街上行人很少,多半是游人。虽然看不到市民的模样,可是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心态是开明和开放的。
比如,一幅街边的壁画。一边是一个手握冰球棍的红胡子男士,另一边则是四个抬起右臂秀肌肉的劳动妇女形象。不知道两幅画之间是否有联系,但是游客看起来,这些女性的形象跟美国的大不相同,一是她们看起来穿着工作服,不像美国女性身着名牌和时装;二是她们“秀”的是手臂肌肉,是劳动健康的美,而不是扭动性感的大腿和露出胸部的乳沟。很像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宣传画:妇女能顶半边天!

又比如,走到一栋新大楼前,明显感觉到是仿古欧式风格的建筑。通往大门的一条走道上,风中飘着三面旗帜,其中一面蓝色写着“黑人的命也是命”,另一面好像是“同志”们彩虹色旗帜,中间的红十字加星月白底旗帜,好像跟中东阿拉伯国家有关?这是我此次美加之行中,第二次看到“黑人”和“同志”的呼声。

马路的一边,是人们熟悉的每个城市都有的教堂。这是一座现代化的教堂,浅灰色乙烯基塑料的墙面,黑色的大门和屋顶,一看就是北美基督教(新教)的教堂,整个建筑透露着简洁直率和效率,高高矗立的尖顶仿佛直接就可以跟上帝通话。不像欧洲或者南美一些个天主教的教堂,庞大庄严、富丽堂皇、堆金砌银、花里胡哨,尤其是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那个圣家堂。
偶尔,游客也可以看到悉尼整洁温馨面貌下一点露怯的贫穷。街道的另外一边,是一栋废弃的大楼,跟周边的建筑颇不协调。我独自走在无人的大街上,虽然阳光明媚,游客可能会有点吃惊地看到路边一些衣物、空酒瓶、塑料袋等流浪汉的遗弃物品,在春风中瑟瑟发抖和随风滚动。
这么小的地方也有无家可归者吗?他们是从哪里移民过来的,还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这跟码头上那一组父子雕像,和他们所提倡的先民们开荒拓土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是不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勤劳和懒惰的人,抑或说富人和穷人?他们难道没有被对面的教堂收容吗?大概上帝也有休息和疏忽的时候。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世界上有阳光灿烂的地方,也有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美国大城市的一些贫民区和流浪汉的集中地,比这里更甚。但是,我看到另一种奇怪的现象,似乎在别的城市,都没有见过。

在电线杆上的电线连接到住户楼房的连接处,电线接头用透明塑胶管在外面包缠。刚开始看到,觉得奇怪,但是觉得可能是个别不懂电器维修的人自己安装的。后来又在别的地方看到好几处家用电线都是如此连接,发现这可能是合乎此地电线安装标准(code)的一种接法。我们现在住地是将各种线路,民用电线、电缆线、电话线等,埋在地下。以前在马州住过那些房子,好像都没有直接从电线杆将电线接到房屋的。用塑料管包扎金属电线接头,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也许是少见多怪了。不过,旅游的一个好处就是开眼界,让自己从熟悉的环境中走出来。
在悉尼小镇停留时间较长。回到船上吃了午饭,又下船看了一些别的地方。悉尼主要的街道上,可以感到历史的痕迹,如银行等一些老式的建筑,绿色圆顶葱头的屋顶和白色花岗岩的圆柱;另一方面,码头附近,也可以看到现代建筑,如商家高层的办公大楼,黑色抛光大理石的墙面和巨大的玻璃门窗。这是一个既保持历史又顺应时代发展的城市。

路上看到一家新装修的餐馆,经营中餐和泰餐。本想进去看看,可惜星期天只有下午4-8开门。路上看到一个东方杂货店,探头一看,一股咖喱味道,原来是印度式的东方。

走到居民区后,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很安静,偶尔可以看到门口停着几辆小车。看到一些有壁炉烟囱的老式砖房,半壁墙面长满了爬墙虎的树叶,不禁想到奥·亨利的小说《最后的一片树叶》。

又看到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房屋,一楼的一面留有待装玻璃的墙面,二楼的骨架结构基本完成,尚未封顶,一个样式新颖的现代化结构。旁边立着一个集装箱,上面有“中国外运”(Sinotrans)的字样,难道悉尼小镇在使用中国的建筑材料,或者节能的太阳能板?这里靠海,中国大陆的触须已经从海洋伸展到加拿大的一个边远小城。不禁有一点小小的惊喜。

在回往码头的另外一条路上,我看见了这头狮雕。狮子被涂成棕黄红土色,模样古朴浑厚,远看不像是石雕,倒像是泥塑。下面铜牌有解释,说明这尊石狮原在路边悉尼加拿大皇家银行旧址。后来在早期工业大革命中被大钢厂迁走。现在复归原位,闲立在海滨大道一旁,看起来老迈龙钟,尾巴耷拉在后腿,不见当年的雄风。石狮背对游船码头,抬头回顾,或许在阳光下,回忆着当年在非洲大草原上雄视一切的景象。
它沉默的目光,并不看着我。而此刻,我是唯一注视着它的游人。
04/28/2024 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