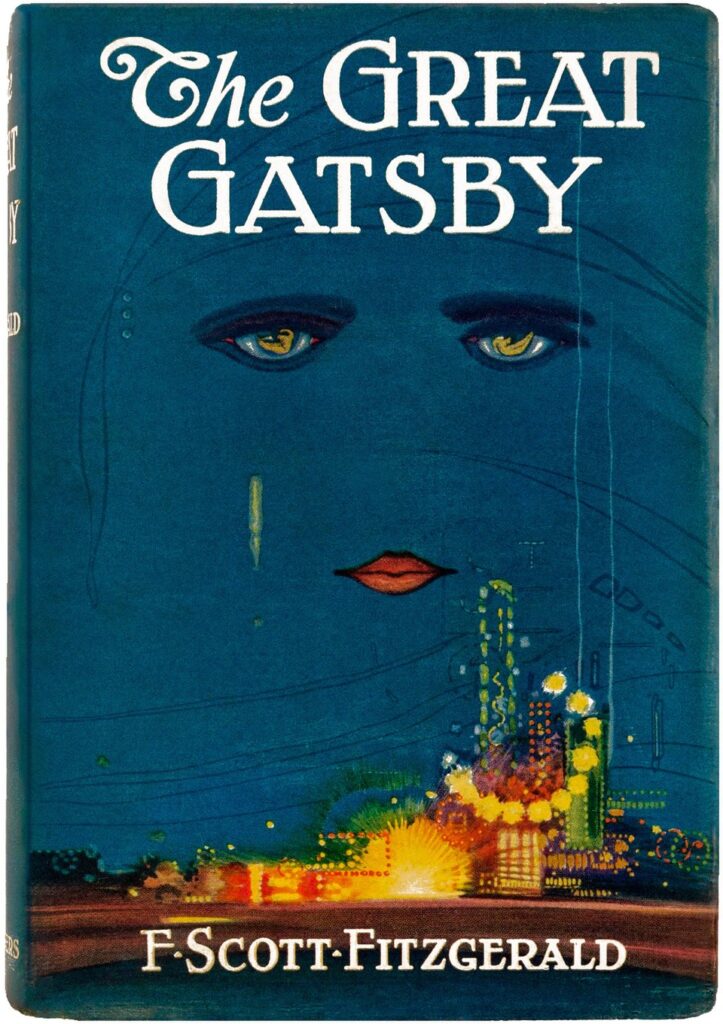在佛罗里达温暖的阳光下回忆往事,华府的岁月总是不期而至。其中记得最清楚的,当属老J——我到华府的第一天,遇到的第一个人。
他来机场接我,开的是大使馆的配车——一辆乳白色的大林肯。阳光在镀铬的车标上跳跃,真皮座椅散发着淡淡的皮革香。八十年代的我们,几乎没人坐过轿车,更遑论这样的豪车。他迎面走来,西装笔挺,领带一丝不苟,开口便是那一句:“来了?还习惯吗?”

老J开着大使馆的林肯车,带我绕华府顺着波托马克河畔转了一圈,白宫、国会山、林肯纪念堂、杰佛逊纪念馆……他指着远处草坪中高耸的华盛顿纪念碑,笑着说:“我刚来时,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站在那儿发愣,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可随即,他语气一转,带着几分认真:“不过,站得再低,也得有抬头看天的胆子。”
我感受到他的心气——不甘平庸,不像我,随遇而安。多年后,他每逢提起华府,总说:“那几年,咱俩傻乎乎地聊理想,倒是人生最痛快的时光。”我才明白,华盛顿的纪念碑下,他藏着一颗不轻易示人的赤子之心。
车窗外的樱花树掠过,让我想起武汉大学的樱花——那是我和老J初识的地方。在英文系读书时,老J就已是年级中的风云人物。他是十年动乱后第一批考上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进了新华社,几经外派,现在是驻华盛顿记者。
初到华府,人生地不熟。暑假期间常常打工到很晚,一个人很是孤独。周末有空老J便来看我,见我一个人呆在住地,就带我去唐人街的餐馆。记得他点了一些中餐,笑着抱怨:“这味道,比武汉还差得远”。
回国后,老J在京城做了几年官,级别不高不低,却总能听到他的名字。他在部委的会议上侃侃而谈,分析国际局势头头是道,连老干部们都忍不住点头。众人眼里,他处处透着聪明和敏锐,也就是英语中的smart and sharp,使得他从一介书生,一路升至省厅级干部。
正是这份“敏锐”,总是让他在风口浪尖上博弈。八十年代末的一场学运的风波,竟让他从云端跌落,从天子脚下被下放到岭南一隅,任了个闲职。他曾经跟我聊起:“这里山清水秀,倒是适合读书。”话中分明听出几分落寞。我知道,这个曾在波托马克河畔杰佛逊纪念馆给我讲解三权分立的读书人,心里始终装着更大的江湖。
即便在地方,他依然干得风风火火。我去探望他那年,岭南的雨雾笼着小镇,湿漉漉的空气让人心头沉重。他带我去看他引进的外资项目,荷兰奶牛在牛栏间低鸣,玩具厂的机器声阵阵传来。他站在招商引资会的讲台上,英语流利如昔,手指轻叩投影仪的节奏,仍是当年在黑板上分析语法时的从容。那一刻,他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老J。可灯光下,他的鬓角已生白发,笑得比从前多了几分磨难后的成熟。
晚间,我们坐在街边小摊,雨棚下的灯光昏黄。我们点了两瓶啤酒,瓶口冒着凉气,沉默半晌后,他低声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断了线的风筝,飞得再高,也回不到原来的天。”他端起酒杯,眼神却望向远处,仿佛在寻找那个曾在波托马克河畔侃侃而谈的自己。我想安慰,却只握紧了杯子,掌心的凉意像他心底的孤寂。那一刻,我才懂,这个读书人心里装的江湖,早已被风雨打湿。
正如老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命运偏爱捉弄耀眼之人。临近退休,老J被部下的一桩贪污案卷入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案子,提前从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那年我拨通他的电话,窗外佛罗里达的棕榈树影摇曳,电话那头的他声音沙哑,像被岁月磨平了棱角:“我问心无愧。”他顿了顿,像是咽下什么,告诉我,有人劝他“花钱消灾”,他却一口回绝,语气里带着倔强:“我这辈子没拿不该拿的钱,凭什么低头?”可随即,他轻叹一声:“只是可惜,没能干完想干的事。”
我知道,他不是贪官。他请我们吃饭,从来不动公款;接待回国探亲的朋友,也从不铺张。可那次通话后,我总想起他点烟时微微颤抖的手指,烟雾模糊了他的眼,他眼底的锐气,似乎被岁月和不公磨去了一角。那一刻,华府的樱花仿佛在心头凋零,只剩波托马克河的流水,默默诉说他的不甘。
十年前,突然得到他在国内去世的消息。一场病来得太急,谁都没料到。
可惜,老J走得太早了。我真想邀他来佛罗里达,逛逛棕榈滩,晒晒太阳,聊聊华府的旧事,再对饮一杯,聊尽我当年未尽的地主之谊。
老J一生几起几落,终究未能享晚年安稳。如今,棕榈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稿纸上,宛如当年国会大厦的阴影漫过我们的青春。他若见到我在阳光之州写下这些文字,想必会淡淡一笑,摆摆手,说:“都是过去的事了。”
可我却忍不住想,华府的那些人和事,是否也在他心里留下了永恒的波纹?或许,人生如波托马克河,奔流不息,却总在某个转弯处,留下几片涟漪,静静流淌在我的记忆里。
作【七律·忆故人】记之。
波河樱雨记初逢
羽扇纶巾意气雄
解说宪章灯影里
招商夷语雨声中
风筝断线云难系
铜雀深春锁已空
今对佛州千顷碧
犹思华府珞珈风
欲罢不能,作【七律·再寄】。
曾约佛州共举杯
谁知云外鹤先回
碑前旧影溶春水
笔底深痕化劫灰
宦海几番潮涨落
京华一梦事成哀
而今唯有棕榈月
犹照当年林肯来
【华府的那些人和事】
06/22/2025 初稿于瓦蓝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