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大街熙熙攘攘 淘书摊人影无踪
一架飞机飞过头顶,震得屋子颤抖。不知是起飞还是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总之是吵醒了梦中人。时间大致为清晨6点半光景。醒了,于是就起来了。
今日的早餐是西式的。冰箱里有昨天买的不含乳糖牛奶,家里有雀巢的速溶咖啡,还有凯辛娜大道(Kissena Boulevard)以前经常光临的那家西点店买的蛋糕和面包。

手机上传来消息,小丫头今天睡懒觉,起来晚了,要晚些时候过来“上学”。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出门看看。有人说,不到曼哈顿就等于没有到纽约市,我说,不到缅街(Main Street)就等于没有到法拉盛。
从我们公寓所在的街道长老街(Elder Street)出来,左手顺着下坡走两个街区,就到了缅街。然后右拐一路往下走,三到四个街区后,就到了皇后区的法拉盛图书馆附近。沿途人行道上越走越拥挤,路边摊也越来越多。鼻子开始感到尘土的气息,这是我们瓦蓝湖的早上所没有的,那里的早上空气是清新的,记得一位来访的朋友说,这里就是一个天然大氧吧。我就是从这里学到“氧吧”这个词的。
渐渐,尘土的气息又混杂着下水道和路边垃圾袋的味道,只往鼻子里钻。在佛罗里达好久都没有戴口罩了,这次到纽约还特地带来口罩,结果出门时忘了带了。法拉盛大街上,满世界的人大都戴口罩。忽然发现,的确是应该戴口罩,即使没有新冠病毒传染之虞,至少可以挡住大街上腐朽脏乱味道!鼻子和喉咙开始痒痒起来。
就这样,走到图书馆斜对面的那家青岛餐馆。以前坐地铁到曼哈顿去时,早上常常在这里落脚。这里的油条可以等着现炸的拿出来,煎饼也是现做现卖,其它的早点中还有领导喜欢的糯米包油条,吃个早点后,还可以带一些生煎包打包,或者点一个炒菜如腰花猪肝什么的带给女儿。旧地重游,青岛餐馆里面更加整洁了。在门口买了两个在锅里热着的蒸玉米,一个黄色,一个五彩,带回去。小丫头和她姥姥都喜欢吃玉米。
大桥下面满满是各种各样小贩的摊位,便宜又实用,可以跟街边众多的一元店抢生意。唯独没有我想看到的书摊子,可能书摊只在周末摆出来,也有可能是书摊挪了位置。那个书摊大多数的书都是跟着时下通俗文化走的出版物,有些恐怕算不上是书,不过,鱼龙混杂,偶尔会有一两本可读之物,就如淘金一般。记得在书摊上曾经淘到一本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横板简体半精装的新书,10美元。这种书在书店里绝不是这个价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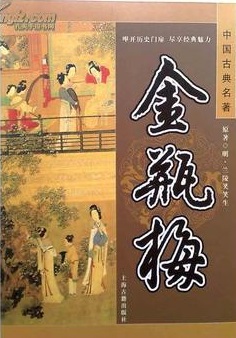
走到铁路桥下,就往回折,这里是缅街和凯辛娜大道的交汇口。从地铁站上来,走凯辛娜大道到我们长老街上的公寓,要比从缅街走近一些,因为两条路在这里形成一个斜对角,像一把剪刀斜着分开了。这里的地标,就是那个在缅街高出地面,须拾级而上的法拉盛图书馆。
跟缅街相比,凯辛娜大道要窄小一些。沿着凯辛娜大道往南走,一路上坡。在缅街相交之处,小摊子和餐馆的密度也毫不逊色。走在摆满路边摊的人行道上,真的是人挤人,大家相互侧肩而过。走了大约一个街区以后,路况渐渐变得好一些。再走几个街道,走到长老街时,才稀松下来。从凯辛娜大道到我们居住得长老街一带,基本上以公寓为主,主要为那些老旧10层以下的红砖公寓楼,也有20多层高较新的公寓鹤立鸡群。
回到家,女婿把小丫头送来了,开始了她一天的私塾生活。
中国胃老饕大享 品不完南北西东
昨日午餐是辛辣的贵州牛筋米粉,今天带小丫头去尝尝一家附近的上海餐馆(Shanghai Eats)。这家店以前来访时是没有的。在昨日早餐的东北快餐店隔壁,一个小小的门脸,跟这条街上大多数的餐馆一样。进门后左手就是收银台,座位左二右三,一个堂吃外卖兼顾的小店。坐下来点了一个雪菜年糕,葱拌面、生煎包和和小笼汤包。几个上海小菜,味道不错。吃到后来发现,生煎包和小笼包原来是一样包子,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蒸的,一个是煎的;一个是头朝上,一个是头朝下。生煎包由于头朝下,把包子的褶子埋在下面煎,而上面则是光溜溜的一个小馒头模样,稍微一凉后,顶部就凹陷了,像个火山口。两种包子里面的馅子一样味道,皮子一样薄,而且一咬汤汁就流出来了。这个有点不地道,应该一个叫蒸汤包,一个叫煎汤包。

晚上女儿带我们到一家具有武汉特色的餐馆“火上面”吃饭。餐馆就在老“豫园”的后面,走路大约20分钟。不过我们老的老小的小,于是乘坐公交车前往。纽约的公交车非常方面,在凯辛娜大道这10多分钟步行的路段,就有几路车两三站停靠。有时天气不好或者人走累了,我们也会坐公交沉代步。
“火上面”也是一个小餐馆,进门三五排座位,里面就是柜台。这里的菜单上有武汉特色热干面,但是我们没有点,在瓦蓝湖家中,常常买袋装的“大汉口”热干面作为早餐。我点了一个豆皮,一个面窝,还有一碗武汉凉面。
凉面是不是武汉特色,难说。但是,却是儿时的我夏天喜欢吃的东西,特别有记忆的味道。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老通城的凉面。其实凉面做起来很简单,有点像热干面的面条,只是面条不用烫,直接往上浇汁即可。凉面的味道主要有醋、酱油、和蒜水。蒜水是其中最有特色的调味,将武汉凉面跟其它地方的凉面,尤其是北京的,区别开来。蒜水不是蒜蓉,是大蒜泡制出来的一种稀释的蒜水。最后加黄瓜丝和胡萝卜丝,撒上些葱花。一角钱,二两粮票,吃在嘴里以醋的味道为主,还有那特殊的蒜味。
这家的凉面还可以,就是汤汁略多了一些。当然,不可能有老通城的凉面味道,留给我的只有回忆。现在,即使在武汉,也不会有人再做这种便宜的凉面了。
豆皮,更是最为典型的老通城记忆了。这家豆皮的馅子汤卤略多,感觉稀了一点,而且颜色有点发暗,因此吃起来,糯米也没有那个QQ的味道。老通城的豆皮是金黄色的,鸡蛋本色带一点微糊,馅子是蒸熟的糯米饭撒上各种佐料和菜码,吃到嘴里软糯且有嚼头。“火上面”的豆皮如果在武汉卖,恐怕不及格。
上次回武汉,在有名美食街“吉庆街”一带,靠中山大道一侧,看到新开的一家老通城豆皮馆。去早了还不到开门的时间,门口竟然排起队来,可见生意之好。排队时,店里还提供免费新沏的大麦茶,服务不错。记得点了一个三鲜豆皮,普通老百姓吃得最多得那种;一个蛋光豆皮,当时较为高档一些的豆皮;还有一个虾仁豆皮,这是领导的偏爱。那叫一个地道和正宗,多年的老味道传承了下来。

面窝,样子看起来还可以,在“火上面”所点的小吃中算是外形最像的了。但是吃起来感觉整体稍微软了一些,大概是米浆中黄豆的比例不对。关键是中间薄的地方不够脆,没有一口咬起来嘎嘣焦脆的味道。如果要打分,勉强也就是70-80分的样子。女儿说,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吃了还想吃第二遍的。我觉得,也是如此。
回家的路上,经过凯辛娜与三福街(Sanford)交界的地方,黑压压满是人。走过街一看,原来在拐角处开了一个小吃夜市。顺着凯辛娜大街一边是两辆烧烤车,车顶冒着浓浓的烧烤黑烟,连带把烧烤的味道散布到街头巷尾。烧烤车后还摆起来一排排简易桌椅板凳,不少人在路灯下或阴影中吃着喝着。

三福街这边黑压压的人就更多了,只是没有桌椅而已。人行道上两三个人搭一张桌子,摆上一个气炉子,就卖起各种小吃来。前面的路摊上有炸臭豆腐的,味道特别大,在马路那边都闻到了。领导买了一盒,一份8美元,还要排队等候15分钟。我们排到了47号。在等待的空隙中,我摸着黑往下走,人群摩肩接踵,我在别人的脑袋背后看商贩在买些什么,有炸丸子的,名为“愤怒的丸子”,有卖小馄炖的,还有各式冰饮料,以及一些说不出名堂的小吃。也有卖小朋友玩具灯具等七七八八的,一直延伸了大半条街。来这里逛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名副其实的法拉盛中国夜市。
看了看,还是炸臭豆腐的生意较好,等我们拿到手时,已经卖到50几号了。摊子上一共三个人干活,一个调料,一个油炸,一个收银。我们买的时候8点刚过,他们的流水已经有$400。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收班,大概生意好,可以做个大几百块钱的。
这些商贩似乎无人管理,人们在街边找个车位停下来,感觉好像随便在家里整一点什么吃的都拿出来卖,有的摊位就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否卫生?法拉盛当局也允许他们这样干?看这这架势,似乎比疫情前还要热闹。
这就是法拉盛,纽约新的中国城。从早到晚,天南地北,除了保证你的中国胃不会在美国思念家乡的美食以外,还会令人感到拥挤得受不了,想要逃避到天涯海角寻个清净的心境。
2022/08/29 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