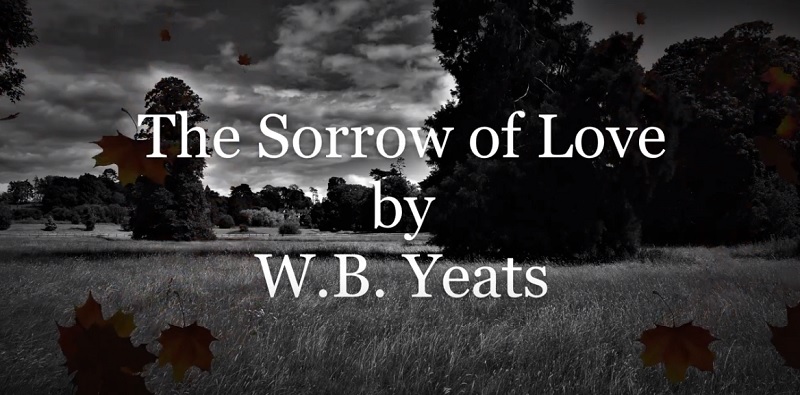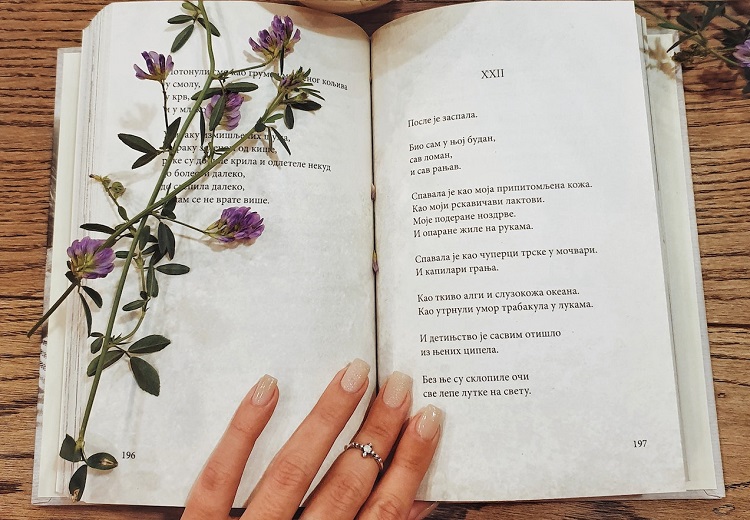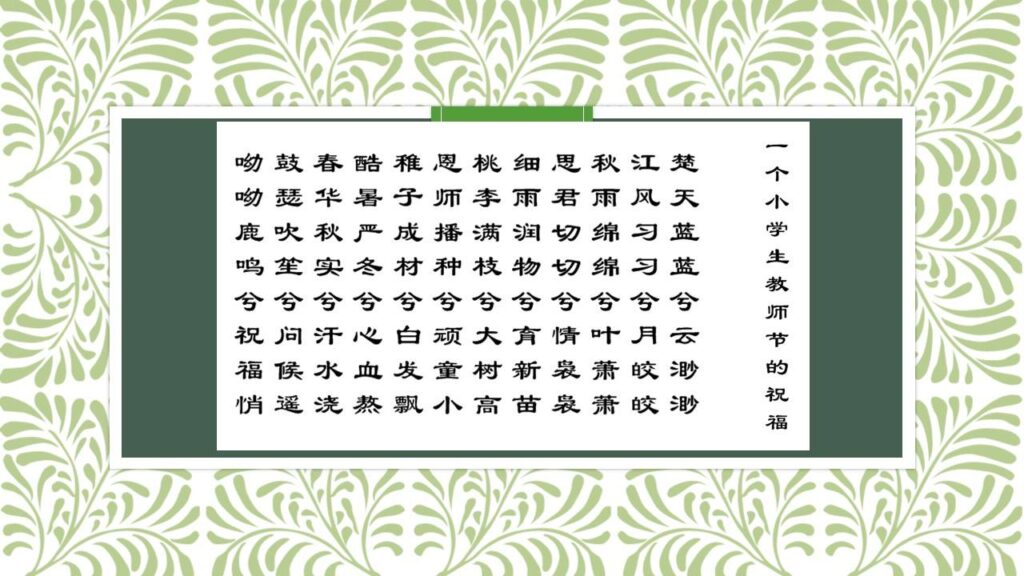如果,整个世界都忘了这一天,美国人也忘不了这一天。
9月11日,爱国者日(Patriot Day)是全国服务日和纪念日,以纪念在2001年在那次袭击事件中丧生的2,977人,以及袭击发生后勇敢的第一批志愿救援者,和他们不畏危险辛勤工作的精神。事件第二年,美国国会设立了这个日子。此后,每逢这一天,美国政府大楼国内外均下半旗致哀,许多公民和企业也这样做,以表示纪念。

今天的电脑桌面图片是布鲁克林大桥,背景是“光之致敬”(Tribute in Light),88个探照灯排列成两列,代表倒塌的双子塔。这个一年一度的装置最初是一个临时展览,从黄昏到黎明,用光柱照亮天空。这是对在宾夕法尼亚州,纽约曼哈顿和华盛顿五角大楼悲惨丧生的人们的鲜明提醒。
为了让人们记住当年志愿者的姓名,有一个问答题是:哪位演员在9月11日之后的几天里担任志愿消防员?
A. 史蒂夫·布西密 (Steve Buscemi)
B. J·W·科尔特斯 (J. W. Cortes)
C. 丹尼斯·法里纳 (Dennis Farina)

不好意思,我知道的美国演员非常有数,题中的几位可能在电影中见过,但是叫不出名字来。正确的答案是A。科尔特斯和法里纳在现实生活中从事警察工作,而布西密则在20世纪80年代在曼哈顿担任消防员。911恐怖袭击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他原本的消防站当自愿者,连续一周工作12小时轮班,在废墟中挖掘瓦砾,寻找失踪的消防员。
看来他的照片后,我认出来他是一个我脸熟的演员,演过许多电影和电视节目,不过他得的奖多半是最佳男配角。
而在一道我自认为有把握的问题上,竟然答错了。大家都知道,911事件摧毁了曼哈顿著名的世贸中心双子塔。那么,取代双子塔的建筑物的名称是什么?

A. 美国之塔 (Tower of America)
B. 世贸中心一号楼 (One World Trade Center)
C. 自由塔 (Freedom Tower)
我到纽约去过多次,也参观过正在建设中的和建成后的新世贸中心大楼,并拍照留念,记得当时的名字就叫自由塔 (Freedom Tower)。结果这道题答错了。

世贸中心一号大楼在开发过程中俗称“自由塔”,但现在恢复了九一一袭击事件之前的原世界贸易中心北塔所使用的名称。原来,我并没有全错,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已。大楼总楼层共地上94层、地下5层楼高,当前该大厦是美国最高的建筑,建筑(包括其尖顶)的总高度达到1,776英尺(541米)。以英尺为单位的高度是有意纪念《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年份1776年。也是纽约第一高楼、西半球最高的建筑,亦是世界第七高的建筑。
爱国者日,人们不仅要纪念911事件的亡灵以及救援的志愿者,更要牢记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战争。

09/11/2023 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