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的一位中学同窗好友,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临省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任教。我那时还在农村,白天在地里干活,天黑了在家里就没有事干。为了打发漫长的黑夜,我会在蜡烛的灯光下看看书,或者写日记,还有写信,给以前的同学和朋友们,其中就包括她。
从她的信中,我渐渐看到,她的学校由一排四五间土房和一个操场(打谷场)组成,连她一共两个女教师。那位老师是一位当地回乡的高中生。每个老师要教几个年级,五六十个学生。不仅要教语文和数学,还要教音乐、图画和体育等课程。

学生们的生活条件很苦,他们自带干粮,常常是玉米饼、红薯干和咸菜,中午在学校里热一热就是午饭。但是,孩子们的学习很认真,尤其是她去了以后,低年级的同学升到高年级了,小学生出去上中学了,孩子们会唱得得歌也多了,也会打球和跳舞了,连以前那些辍学的孩子们又复学了。信中让我体会到她跟孩子们相处中,尤其是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所带来的满足感。
我给她的信中,会聊到“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那部50年代上映的苏联影片,满是丁香花气的春夜中少女的初恋、荒凉的村野与破旧的教室里孤身女子的搏斗,这些都曾经热血沸腾地感动了我们这代人。不过,等我们到了农村,现实像冷水很快就熄灭了我们心中的那股虚火。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周而复始,往日的理想消失在黑夜的寂静中。我们的青春难道就这样一点地耗费在这里?
面对我的消极,她给我写过一封回信,讲她在师范学校上的第一堂课。

老师在讲台上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壹圆的人民币纸钞,问道:我把这一块钱送给你们,有没有人要?同学们犹豫了一下,慢慢地举起手来。
老师把人民币在手中捏了捏,搓揉成一个小球,摊在手掌,然后又问学生们,这样你们还要吗?同学们再次纷纷举起手来。
老师把揉成一团的钱扔到地上,然后用脚踩上去,将人民币踩成面貌全非的一个瘪瘪的纸饼。用两个手指夹着,继续问,还有人要吗?一些同学犹豫了,仍然还有许多同学举手。
老师接着说,为什么这张人民币变成这样了,还有人这么多人要?因为它有自身的价值。不管你们将来的生活中将会遭受什么挫折和痛苦,只要你们坚持自身的价值,就对得起自己,就会得到人们的欣赏和尊重。
这堂课给她的震动和启发极大,她在信尾告诉我。这也是她除了“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以外,坚守乡村小学的支柱——坚守自身价值。然而,我却没有她那么坚信,因为当时的我,还不清楚我的自身价值是什么。
几年后,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通过全国高考,我从农村考上了大学。我的信中开始充满了丰富又紧张的大学生活。然后,我有了心仪的白马王子。渐渐地我们之间的通信减少了。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通信就中断了。
毕业后,我留校当了教师,再后来,又出国了,我们之间就没有了联系。结婚生子后,家庭忙忙碌碌,几乎把她淡忘了。
从同学那里听说,她后来离开了那所乡村学校,也回城了,一直在家乡一所中学任教。退休后,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日子过得还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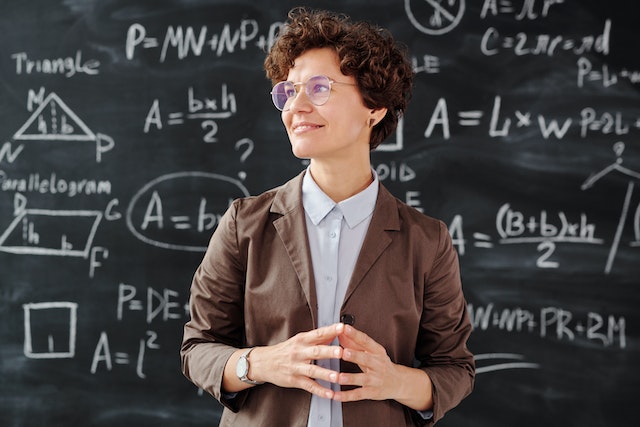
一次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喝酒聊天,“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聊到当年农村的那段往事时,她有些嗨了,自己当初真的是想立志扎根农村教育,做个瓦尔瓦拉那样的平凡乡村女教师。结果,最后辜负了孩子们和乡亲们的期待,还是回城了。言谈中颇有些自责地感叹。
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弄明白,大概是一种追求吧。
另外,社会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是否也要随之改变,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07/24/2023 于瓦蓝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