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静静地坐下来,读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不是脸书上那些短短的视频节目。开始看起来有各种题材,现代、古代、国产、外国、武打、生活、科幻、穿越,关键是短小,十分钟左右讲完一个故事,潮起潮落,短平快。当然这都是晚间脑子疲惫,写完了杂感随笔后,让脑子放松,在睡觉的“轻松一刻”的时间。这些小杂碎,可以不断地看下去,一个故事开始,很快就推进到高潮,意料中的和意外的结局,过不了多久就会到来。兴奋点马上又被另一个噱头吸引过去。

时间一长,重复类似的题材和故事就开始出现。就像排球场上接过一传的球后,不再将球做一个好的二传给主攻手,而是直接在二传的位置上将球扣死在对方的场地上。不待看完这一集,而是将屏幕下滑到另一个故事。
家中书柜里我自己的书不太多,大概占有一个书柜的三格半,另外的两格半则是其它的文具纸张和一些时光积攒下来的杂七杂八册子。另一个书柜是女儿留在这儿的一些旧书,估计她不会再看,但是也不允许我们将其处理掉,属于曹操的鸡肋之物。还有领导近来购买的各式画册和大作,在六层的书柜中占了四层。最下面的一层是过时的工具书,辞海、辞源、几本厚厚的英汉、汉英大辞典,三十年前还是个宝,偶尔会拿出来查查翻翻,现在应该不会再用到它们了。互联网早就将它们淘汰了,更不用说AI人工智能的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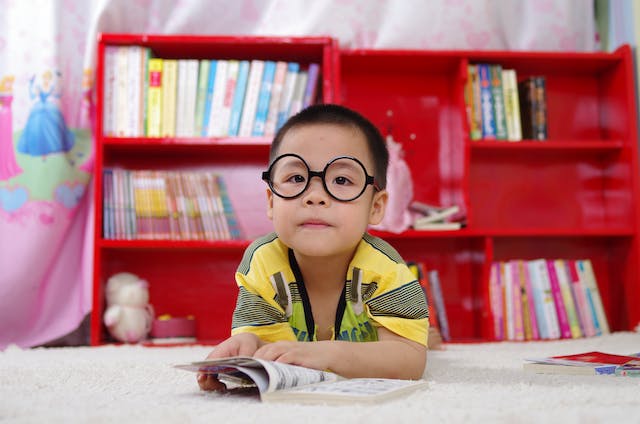
属于我的三格半书中,有一格是朋友和文友的书籍,诗歌、散文、小说都有,这些书都看过了,搁在最上一层。第二格一半是诗歌,现代诗中有当代口语诗和顾城、海子的朦胧诗,国外的有普希金、海涅和泰戈尔的诗集,古诗词有入门的诗经、唐诗宋词和一些名家的诗论。第二格的另外一半是莫言的十几本小说,不是我买的,是国内某个机构赠送给我们这里的文学组织,而这些书太多,我们这些个海外文学“协会”大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Office),所以记分发给协会的成员。轮到我时,想要的“好书”早被别人挑完,莫言虽然是国人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的高密乡的土东西在海外的“文化人”中,并不待见。于是就落入我的囊中,我已经看了其中的一半。
第三格有一半是捡垃圾收来的古旧书,计有儒林外史、七侠五义、聊斋、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家春秋、一套金陵春梦等,另一半是在纽约法拉盛书摊上淘来的的金瓶梅和各版的石头记、红楼梦以及民国文人周树人、徐志摩、朱自清的散文,当然还有鲁迅的杂文。
剩下的半格有一半也是文友的书和几本杂书,如李悦口述往事,这本书在大陆是禁书,在香港发行过,基本售罄,还是从是作者女儿手中获得。每每坐下来,看看书架,那几本“藏书”实在是很可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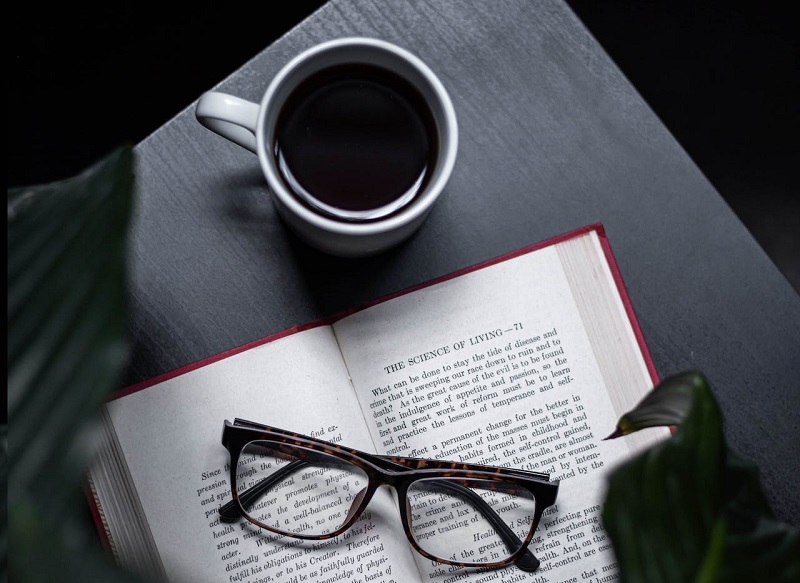
不过,互联网改变了“书”的形式和“书架”的形式,从硬到软。人们读书基本都在电脑的大屏幕以及手机和iPAD之上。我电脑的文件夹里面,长长一串的“书”文件,替代了我的可怜的书架。基本上我都是在电脑上读书,读大部头的书,大部分都来自网上书店的电子书。比如我正在看的“张爱玲作品集”。
原本打算讲讲读张爱玲的随感心得,看到她云里雾里东讲西讲的写着她的散文,我也就被她带了过去,从读书闲扯到书架。一抬头,12点钟了。眼皮沉重,困意袭来。
周末的晚上,6点半到9点半是我们掼蛋俱乐部的活动时间。我们队今晚获胜,虽然我一盘都没有拿过上游。回来看了两篇张爱玲的散文,接着写随感,不觉就到了第二天凌晨。超过上床时间,罢笔,睡觉。
新年第一个周日的早上
一出门天、地都是干干的
只有乌云和风在捣乱
刚走了不多远的路
就把昨天没有下完的雨
稀稀拉拉地洒在今天
也把明日才会落下的残叶
湿漉漉地刮到今天的地面
转身往回还没有走到家门口
抬头碰到云开雾散的今天
低头看见地上残留的水印和落叶
映证着刚才的昨天和明天
01/07/2024 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