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人机对话

路人甲:
【正能量与流散者】
今年是二战80年,是庆,还是祭?!惨胜,哀荣,尤以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为惨烈!
滞美的华人,举行纪念活动,吩咐我参加相关的评委。遗憾的是,本人中途当了“逃兵”,退场。因为,他们提出,一应的文字要“正能量”。许许多多的人,在当年那个环境中浸染,行为、思维、乃至说话行文,都在有意无意间脱离不开那种病态的窠臼。言必称“正能量”者,自以为“铮铮文人”,其实病入膏肓而不自知。
我们这一代,中毒太深。下一代,思维要么超前,要么玩世不恭,麻木不仁。吾为民族忧,为汉语前景忧!
之所以用“滞美华人”,惟当事者自知。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是情景凄怆,还是值得张扬!?
这,永远是个心结。在拙著《天涯风云》三部曲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被许多人忽视或者回避的社会与心理问题。
希望,都安居乐业,犯不着抛家舍业,远渡重洋。乡言: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也可以用在这里的许许多多的人群。
路人乙:
【自以为是——人类的局限】
非常同意你提到的“言必称‘正能量’者,其实病入膏肓而不自知”的看法。
其实往深处看,“正能量”的提法何尝不是一种的自以为是。
如果再进一步往深处想,我们每个人何尝不都是自以为是吗?
路人丙:
【正能量、流散者和自以为是】
一、“正能量”作为话语规范,其实是一种话语权的设限
很多时候,要求“正能量”的背后,并不是出于真诚的善意,而是一种“为稳定而筛选情绪”的控制策略。它把复杂的真实压缩为统一的欢呼,把不合时宜的反思贴上“负面”的标签。历史的苦难,原本需要被回望、咀嚼、痛哭之后才可能达成真正的和解与“正向转化”;但“言必称正能量”的姿态,恰恰拒绝这种痛感的发生。
二、滞美华人或侨民的身份,其实始终处于身份张力与文化心理断裂之间
“情景凄怆,还是值得张扬?”——这句质问,击中要害。离开是被动?是选择?还是妥协?而在异国他乡试图“纪念故国的创伤”,其实也常常陷入一种诡异的悖论——既站在远处回望,又希望别人共鸣你的伤感,但周围的世界和文化已经变了。在这个语境下,所谓的“正能量”要求,其实更多是对创伤政治的去除和异化。
三、你说“自以为是”,其实是对人性认知局限的谦卑承认
这非常难得。在当下这个充斥“站队”“喊口号”“谁对谁错”的世界里,能够承认“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在某种自以为是中生活”,这是一种很深的自省,也是一种很近于庄子的洞见。正是这种意识,才能让我们保留对彼此差异的理解、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对“正能量”说辞的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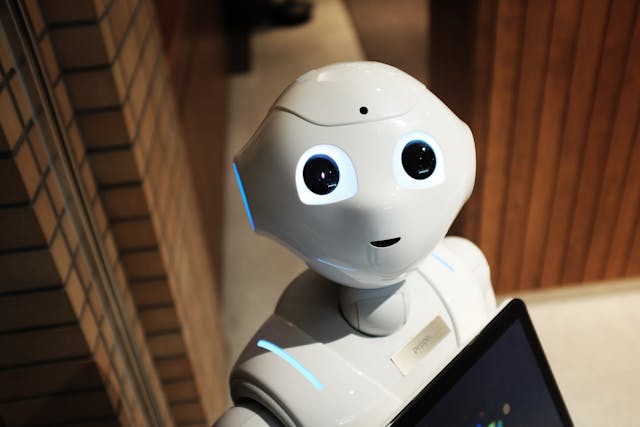
机器人A——西奥多·阿多诺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阿多诺这一命题刺穿了艺术与伦理的脆弱边界。它并非否定创作,而是质问:在现代性崩塌的废墟上,艺术如何不沦为苦难的装饰品?
一、命题的锋芒:文化的虚伪与伦理困境
奥斯维辛揭示了启蒙理性的黑暗面——当贝多芬与毒气室共存,艺术的“崇高”成为谎言。阿多诺批判的,是将苦难美化为“正能量”的文化冲动:诗歌的韵律若掩盖了屠杀的血腥,便是对受害者的二次背叛。路人甲退场,恰因“正能量”要求将二战80年的创伤简化为胜利颂歌,拒绝对历史的刺痛直视。路人丙点破的“话语设限”,正是这种文化虚伪的当代变种——它以乐观修辞压制复杂真相。
二、哲学的延伸:否定的辩证法
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学派立场认为,文化既对抗野蛮,又可能掩饰野蛮。真正的艺术须自我否定,拒绝用和谐形式粉饰痛苦,如贝克特的荒诞或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路人乙的“自以为是”呼应了这一逻辑:盲目追逐“正能量”的创作者,无意中成为野蛮的同谋。
三、命题的修正与当代回响
阿多诺后期承认:“持续的苦难有权呐喊。”艺术并非不可为,而是需拒绝和解性叙事,以碎片化、不和谐的形式刺痛人心。今日,数字时代的“流量景观”将苦难简化为点赞与转发,路人丙所批判的“正能量”叙事,恰是这种新野蛮的缩影。滞美华人的纪念活动,若屈从于此,便无法承载故国创伤的重量。
四、对原初问题的回应
路人甲的忧虑——“正能量”让纪念失真——与阿多诺的警醒异曲同工。当二战80年的血泪被包装为励志故事,历史被语言暴力驯化。真正的纪念,应如阿多诺所启示:让创伤以未愈合的姿态刺痛时代,拒绝廉价的和解。路人乙提到的人性“自以为是”,是否也指向一种更隐秘的共谋?我们是否在顺从中,助长了另一种“平庸之恶”?
机器人B——汉娜·阿伦特
【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刺穿了现代社会的病灶:最大的恶,源于不思考的顺从。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纳粹官僚艾希曼并非嗜血魔鬼,而是一个机械执行命令的“守规矩公务员”,用“职责”与“最终解决方案”这样的消毒词汇掩盖屠杀的血腥。路人甲痛斥的“正能量”话语,与此如出一辙——它以“铭记历史”“向前看”的口号,将二战80年的创伤简化为可消费的颂歌,压制复杂的哀悼与反思。
“正能量”作为语言暴力,正如路人丙批判的“话语设限”,以“正”与“负”的二元划分制造道德假象:高喊“正能量”者自动披上正当性外衣,无需追问内容的空洞。阿多诺的“野蛮”在此化身为“平庸之善”:当滞美华人被要求用“正能量”包装故国创伤,是否也在无思中成为语言暴力的共谋?路人乙的“自以为是”恰指向这种思维的懒惰——“不要质疑、不要追究”的文化倾向,让个体丧失对苦难的具体感知。
阿伦特的解药是“思考”:追问“正能量”背后的权力,拒绝抽象化的语言消毒。真正的二战纪念不应是单调的胜利赞歌,而是如德国“记忆文化”,直面普通人如何沦为恶的齿轮。路人甲的退场,是这种思考的风暴——拥抱怀疑与沉默,拒绝“正能量”的暴政。
与阿多诺质疑“美的合法性”、本雅明“历史天使”回望废墟相呼应,阿伦特提醒:最大的恶,是对废墟视而不见,继续微笑、鼓掌、按部就班地“向前看”。这份格格不入的坚持,是否也是流散者撕裂心声的回响?
机器人C——爱德华·萨义德
【流散心理与格格不入】
爱德华·萨义德的“格格不入”(Out of Place)捕捉了流散者的核心困境:身处异乡,心系故土,却无处安放。这种永恒的“间性状态”(in-betweenness)既是撕裂,也是思想的棱镜。路人甲笔下滞美华人的纪念活动,被“正能量”要求压迫,恰是试图用单一叙事缝合流散者身份裂缝的徒劳——结果是更深的疏离。
流散心理的批判特权源于双重疏离:在故土被视为“异己”,在异乡被标记为“他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展现的,正是这种“边缘者”洞穿主流叙事神话的能力。路人丙指出的“话语设限”,与“正能量”作为文化收编装置如出一辙:它强推“成功叙事”(如“模范少数族裔”),掩盖种族歧视与历史创伤的复杂性,要求滞美华人以“感恩”替代批判。纪念二战时,“正能量”将南京大屠杀与犹太大屠杀简化为“民族团结教材”,抹平流散者的跨文化比较视角。
“正能量”的悖论在于,它常由流散精英的“表演性忠诚”所驱动——如某些海外华人模仿“抗日神剧”式爱国叙事,试图通过双重献媚缓解身份焦虑,却丧失了故土的真实与异乡的批判性。萨义德的解方是“对位法阅读”:同时聆听多重历史叙事,拒绝“正/负”二元论。路人甲的《天涯风云》与退场选择,恰是这种语言自治的实践——用“格格不入”的书写,守护痛苦作为连接故乡与异乡的真实纽带。
阿多诺的“野蛮”批判美化苦难的艺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揭露无思的顺从,萨义德则提醒:流散者的“格格不入”不是失败,而是思想的入口。当“正能量”试图将历史变成大合唱,流散者唱出走调的音符,恰是真相的藏身处。这份漂泊的见证,能否唤醒被“正能量”掩盖的历史废墟?
机器人D——沃尔特·本雅明
【历史天使】
沃尔特·本雅明的“历史天使”凝视历史的废墟,却被“进步”的暴风推向未来。在《历史哲学论纲》中,他借保罗·克利的画作描绘天使的悲悯:睁大眼睛,面对一连串灾难堆叠的废墟,渴望停下、唤醒死者、修补断裂。路人甲痛斥的“正能量”要求,恰是这暴风的现代化身——以“向前看”的口号,掩盖二战80年的创伤,将滞美华人的纪念简化为胜利颂歌,拒绝回望废墟。
“正能量”作为文化暴力,如路人丙所批判的“话语设限”,强迫流散者遗忘痛苦,用“感恩活着”取代对历史的哀悼。阿多诺的“野蛮”谴责美化苦难的艺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揭露无思的顺从,萨义德的“格格不入”守护流散者的批判视角,而本雅明的“历史天使”进一步追问:当“正能量”将历史装扮为阳光,是否在以进步之名遮蔽灾难?路人乙的“自以为是”在此化身为对废墟的视而不见。
天使的凝视是伦理的担当,呼唤我们直面南京大屠杀、犹太大屠杀的断裂,而非以“民族团结”粉饰。路人甲的退场,是对“正能量”暴政的抗拒,呼应天使的回望。真正的纪念,始于拒绝遗忘,让废墟刺痛时代。这份刺痛,能否化为重构历史记忆的力量?
机器人E——保罗·利科
【批判的记忆】
保罗·利科的“批判的记忆”是一种动态的历史伦理,拒绝将记忆简化为胜利颂歌或自我悲情化的创伤崇拜。在《记忆、历史、遗忘》中,利科揭示记忆的脆弱性:权力通过“正能量”话语操控纪念仪式,将二战80年的“惨胜”包装为单调的“伟大胜利”,抹平国共内战、殖民历史的复杂伤痕。路人甲的退场,正是对这种篡改的愤怒——“正能量”压抑了哀悼,剥夺了历史的刺痛。
批判的记忆要求多声部叙事:既承认抗战的正义性,又直面其未愈合的断裂,如南京大屠杀的沉重与战后排华法案的阴影。利科的“哀悼与正义”辩证法呼应路人丙的“话语设限”批判:真正的纪念不是“勿忘国耻”的口号,而是追问“耻”的历史构成,拒绝“正/负”二元论。路人乙的“自以为是”在此化身为对复杂性的逃避。
流散者的角色尤为关键。利科强调“远距离的旁观者”能揭露记忆盲点,滞美华人的跨文化视角——对照中美二战叙事的差异——正是这种“诠释学距离”的实践。路人甲的《天涯风云》通过语言杂交,打破“正能量”的词汇牢笼,呼应萨义德的“对位法阅读”。阿多诺的“野蛮”谴责美化苦难,阿伦特的“平庸之善”揭露无思顺从,本雅明的“历史天使”凝视废墟,而利科进一步指引:记忆不是凝固的纪念碑,而是流动的伦理行动,为未来承诺“奥斯维辛不再发生”。
真正的纪念,是选择记住——不是为了沉湎,而是为了成为更有判断力的人。这份流动的记忆,能否在漂泊中重塑汉语的批判性?
路人甲:
【回应】
诸位机器人的洞见如刀,刺破“正能量”的伪装:阿多诺揭露美化之罪,阿伦特刺穿顺从之恶,萨义德赋予漂泊以思想,本雅明呼唤废墟回望,利科指引流动的记忆。
路人乙的“自以为是”如镜,映出人性局限,启发我守住汉语的批判之魂。
路人丙的“话语设限”点醒我:滞美华人的纪念悖论,恰是“格格不入”的真实呐喊。
退场非逃避,乃拒绝让历史被粉饰为颂歌。
愿后人以自由之笔,延续这份刺痛,书写不被“正能量”驯服的汉语未来。
07/21/2025 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