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散步回来,就坐在电脑前“看书”。退休的生活很随意,也很任性。想干怎么就干什么。
我这个人,大概属于“散射性”思维,从小就没有常性。小时候上课,一开始可以老老实实听讲,到后来就坐不住了,当然,这不可能是老师讲得不好的原因。然后,一会儿跟“同桌的你”悄悄地讲讲话,一会儿跟邻桌的他偷偷地分享一点“异想天开”的发现,如地上的一只蚂蚁可以扛着比它体积还要大的饭粒横着走路,窗外屋顶上的那只公鸽子又换了一只瓦灰色的母鸽子,原来的那只是雨点。
直到经过无数次社会的磨练——被老师批评、派同学给家长告状、被家长训斥,渐渐知道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是,在课堂上也可以“不逾矩”了,可是,人坐在那里,两眼盯着黑板,心却飘到了窗外那个大千世界,耳朵里一边是老师的讲课,另一边却是树上的鸟叫(麻雀还是燕子?)和大街上的车辆来往的声音(小汽车公共汽车还是电车?)。毋庸置疑,这是进步,至少不会干扰课堂,不让老师分心,也不会打扰周围的同学。但是,人端坐在教室,心不在焉,思维散射了,这却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及至大学毕业,走上讲台,面对堂下窃窃私语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学生,我从不责怪他们,因为,我也有过“当年”,也有思维散射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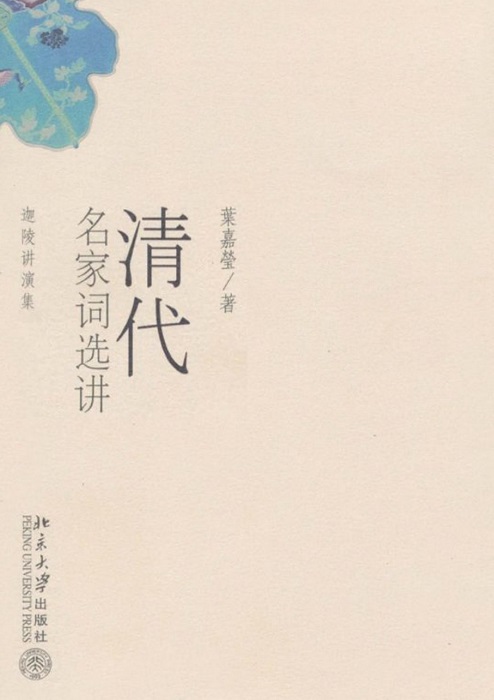
其实,又何止当年,基因里的东西,生来如此。此刻,我眼里看着王鼎钧的【怒目少年】,心里却开了小差,想看看叶嘉莹先生的【清代名家词选讲】,原因之一,是从来没有系统地了解过清代的词人与词作,另一个原因是,是在目录中没有看到纳兰性德的词,而这是我所知道到少数有名的清代词人之一。不免觉得奇怪,似乎要谈清词,就不能不提纳兰性德,难道纳兰性德还称不上是清词的名家,还是叶嘉莹先生另有看法?
读完序言,才知道这是叶嘉莹先生在新加坡大学讲学的讲课录音整理。由于学时限制,只讲授了原定十四人中的一半,其他的一半由学生自己阅读教材,然后在辅导课中讨论。而纳兰性德就在没有课堂讲授的几位清词作者之中。
不过,在叶嘉莹先生的另外一本书【清词丛论】,有专文《论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谈及纳兰性德,以及如何欣赏、理解和诠释诗词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于是,又“散射性”地跳着看了。内容太丰富,涉及到青原惟信禅师所提出的悟道的三般见解,即开始见山就是山,中间见山不是山,最后见山还是山。还有西方学者葛德谟的“合成视野之说”理论,以及姚斯的阅读视野的“三个阶层”之说。

纳兰的词,读过一些。每个人在阅读时都有由其个人生活经验与读书经验所形成的⼀个视野水平,他对作品的理解就是透过他自己的这个视野水平而理解的。是对于作品的形式和声音等各方面直觉的美感的感受。是谓“初时看山是山”的初级感觉。
而禅学、美学和哲学这些抽象和“形而上”的的东西,一般都比较玄,不容易理解,须得静下心来,仔细研读和揣摩。今天就囫囵吞枣,待以后通过“理性的对作品内含的反思和探索”慢慢化之。至于,是否能达到“结合文化传统的历史视野来阅读”,通过这个所谓“合成视野”达到较正确的理解,那就不知道了。
05/05/2023 周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