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极必反。正应了那句话,昨日的高温如夏,换来今天早晨的一场春雨。看到湖面上的水圈,想起小时候学的一个谜语:千条线万条线,掉到水里都不见。然后续一句残诗:(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小雨推迟了例行的清早散步。早饭后,就渐渐停了下来,我们得以继续散步。只不过稍微改变了一下路径,从南门方向,改往西门的菜园。雨后的园子里蔬菜雨后苍翠欲滴。几块园子中又新增加了可以让瓜果爬藤的架子,白色间或绿色的棚架,让整个菜地春天的气息更浓。残诗于是又衍生出新的结尾:细腻春风今又至,换了田间。
一百年前的1922年,人类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文化对那个动荡年代的开始反思,并做出了重要的回应。纵向观察历史,人们通常的回顾方式,这是文化史发展中的一个喷发期。从横向上来看,则是春城无处不飞花。世界不仅从爱因斯坦那里知道了《相对论》,更是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两个前无古人且难以读懂的杰作: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看起来晦涩凌乱被认为是意识流的经典作品;还有艾略特对西方幻灭绝望的《荒原》(Waste Land),一部整个20世纪历史上最有名的长诗。
这两部作品的伟大之处之一,不仅在于它们的内涵晦涩难懂,跟在于外表上充满了人人都能欣赏的优美传统的文学语言。乔伊斯和艾略特都知道该如何取悦和挑战读者。这不仅是它们在当时富有新鲜感的原因,也使得它们在后来的岁月里被人们反复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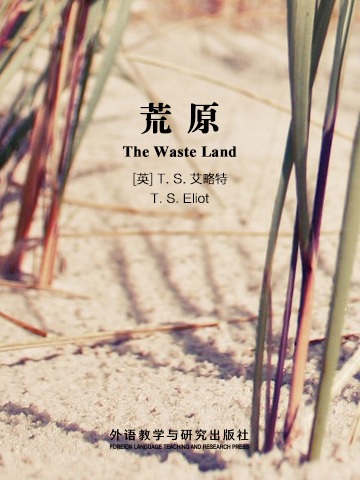
我硬着头皮读过艾略特的《荒原》,从“四月最残忍”开始,到最后的“平安。平安。平安”。看过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小说结构,全书三部分十八章,每一小时写一章,展现发生在都柏林一天十八小时中的种种事情,结果和大多数读者一样,云里雾里。我坚信,他们写的东西,大概不是让我们这种下里巴人级别的人读的,所以,作为下里巴人,我们亦应该有自知自明,就让那些自以为够阳春白雪级别,能读懂的人去伤脑筋或者是欣赏去吧。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会重新打开《荒原》,追随《尤利西斯》一天的经历。
忽然想到,有些东西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平凡的人们搞不懂,譬如爱因斯坦那道看起来极为简单的公式 E = MC²,如果换成 X = 1+1,就不显得伟大了。
于是,我转向世界的东方,1922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时代。胡适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一次以“史”的角度尝试研究现代文学。鲁迅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一篇篇作品如《狂人日记》、《故乡》、《孔乙己》、《阿Q正传》等等,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让国人开始对吾国吾民“国民劣根性”的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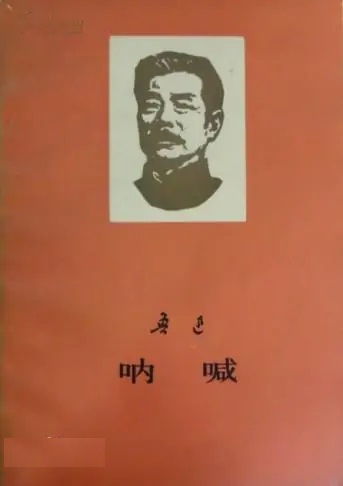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我是从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知道他的。就像乔伊斯和艾略特在他们凌乱、混乱的结构中所做的那样,在日本摆脱了几个世纪的孤立主义后,将新旧融合在一起。芥川龙之介用支离破碎的叙事方式重述了一个12世纪的民间故事,其中一些观点和目击者相互矛盾。《竹林中》挑战了真相可以被明确知晓的观点,并削弱了叙述者权威的概念,成为后来一种流行的讲故事方式。
回到《圣经》上那句“太阳底下无新事”的话,我们每天看到的事情都是以前做过的,已经有的事情今后还会有。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徐州丰县的锁链后面,看到100年前国民劣根性的影子。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女孩,1989年出生,比我的女儿还要小。此前我已经离开大陆。她的中国,比我的新中国还要新中国。她的老家在丰县隔壁的枣庄农村,本人有18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后来高考离开农村。据她讲:
在我老家几乎每个村里都有这样的拐卖妇女,清一色“云贵川”过来的,我们叫“蛮子”。所有人都认为光棍买到媳妇结了婚生孩子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从来都如此,也就麻木到认为合情合理。你跟我说官员渎职和拐卖罪,底层人民的法律意识,极端淡薄,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啊”的无知。
很多人的思维里,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买回来的媳妇,你有什么自由和人权可言?我买来的你,你就是要给我生孩子的,你竟然敢跑?!没生孩子就逃走,本来一个光棍没有老婆就够丢人现眼的,你再跑就是再次伤害和侮辱他。乡亲们自然对他非常同情,还会自发地去帮助他看着甚至找回这个女人。所以,被抓回来肯定就是会被打,然后监禁当然是常规操作,反复跑,反复被抓。再所以,打到精神失常,拴起来,方便生孩子在情理和逻辑都毫无毛病;生了孩子即使逃走了,他们会自我安慰,至少留下来了个属于自己的“蛋”。
女人要学历有什么用?长得高,长得胖,年轻能生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贫穷的繁殖欲旺盛的山东农村的最佳择偶标准。很原始是吧?如果你不理解,我推荐你去读山东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蛙》,在山东高密农村,侏儒的女人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生下小孩。
时间这个东西加上思想这个玩意放在一个脑子这个固定空间里长期发酵,好了叫熏陶,坏了叫陋习,长远讲就是风土人情,大家习以为常,并且代代相传,比世界遗产还要顽固不灭。
看到这里,让人细思极恐。在经历WG后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兴奋地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憧憬中国未来发展的时候。于此并行不悖的陋习,拐卖妇女还在中原大地的农村里盛行。枣庄不就是“铁道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地方吗?有火车的地方应该不会像大西北黄土高原窑洞,或者是广西十万大山那么偏远和闭塞,这种事情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讲到她是怎么跳出那个重男轻女的圈子时,作者说道:
我那个时候很小,听到她(母亲)讲这种故事,完全无法带入和理解,我内心对这种命运瑟瑟发抖,无比战栗和恐惧。我发誓我一定要离开那个地方,离开农村,摆脱这种生到有男孩为止的命运,我常说这是第一次如此强烈的要改变命运,要捍卫我那个时候无法理解的“子宫自由”这个议题。
一个人从原来的地方,要爬出来,站起来,就会有无数的人用各种方法拉住你下去。
我拼命挣钱学习,我用力扒开他们拉我向下的手,我极力与他们撇清关系,我对他们这种恶臭言论恶语相向,凡是让我出钱贴补弟弟的亲戚,我一概不再联系,凡是封建思想残余的亲友,我一概不理。
生在农村的女孩千千万万,却不是每个女孩都有我和我同学这样的运气和能力,她们的命运还在重复。
在那种大环境下,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帮凶,所有人的眼耳口舌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让她逃无可逃。特立独行要有巨大的能力,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那种环境中并且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甚至大概率是失败,失败的代价就是远走他乡。
我的家乡不是最穷的,我听过见过更多苦难的故事。再回头看现在的农村,更加可怖,隐患丛生,因为重男轻女,光棍比之前还要多得多,年轻女性(的子宫)几乎成为稀缺品。离了婚生过孩子(哦,对了,生了孩子你可以走,但是孩子要留下)的女人也有人争先恐后的要,以前这叫放荡,现在没人指点。是的,只要有子宫可以生就行,甚至可以不工作,可以光明正大地啃老。
这些全是最真实的描述,毫无夸张。
最后,她把解决问题的答案,又还给了鲁迅。
鲁迅在一百年前就给出了答案:思想更新,唯有教育。发展教育,发展经济,让更多的人思想开始觉悟,让更多的人沐浴光明,因为这是她们一出生下来本该就拥有的权利。
鲁迅《呐喊》一百年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难不成我们还要继续对国民进行启蒙和大声呐喊吗?
2022年2月13日 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