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淅淅沥沥,坐在后院纱墙内,读书。

一本吴均尧的散文集《热地图》,在腿上摊开,在朦胧中飘着金门岛的风。滴滴答答的雨水,落在草丛和池塘里,似乎带有金门海水的咸腥。雨中读散文最好,断断续续、星星点点,随风飘逸,可短可长、可行可止。一段终了,端起咖啡,喝上一两口,把故事和作者的感触,溶化后吞下。眼望窗外,迷迷蒙蒙,想像金门的山路,在风雨里会是什么样子?于是,又低头读下去。
读吴均尧的散文,喜欢他在段落后,尤其是在文章结尾处的感想。时而空灵,时而深邃,时而温馨,常常出其不意。散文和诗歌,其比兴和意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吴曾提到,青年时曾经热衷于诗歌,后来发现不是所长,遂改为散文和小说。总觉得他的散文中,飞舞着诗歌的精灵。又或者说,将诗歌的灵性放到散文里,是一条美化散文的蹊径?
随便举几个例子。譬如:
- 谈到饥饿:“饥饿竟会这么深刻:而一种匮乏,也深深地,寄居在饥饿里了。”
- 谈过去和曾经:“时间跟我,舒服地挤在一块儿。”
- 话别青春:“我心中的链条断了,我轻轻地说了声,‘再见’。”
- 回忆童年:“原来,我是锄了一个黑洞,埋了童年。”
- 讲拜佛的无聊:“无聊的雾啊,让什么都看不见,没有蟾蜍跳进中庭,只有一对声音,在厨房又眨又跳。”
文中,经常会看到名词动词之间新颖的组合,具体到抽象的变化,还有从生活到想象的跳跃。
看他的文章,体会台湾作家的文笔,觉得跟大陆的现代和当代文章不一样,有承袭民国新文化的传统。常常会在字里行间,品出些鲁迅、朱自清、周作人等三十年代文人的味道来。这种味道,在大陆的文章中,较少看见。看来,两岸华人文学自1949年以后,逐渐承袭发展出不同的风格。除了简繁体、横竖排版,遣词造句,个中内涵和表述趋势也确有不同。细雨中,慢慢品味,也蛮有意思的。
读着读着,就迷失在金门、三重和台北贫瘠与繁华来回交织的热地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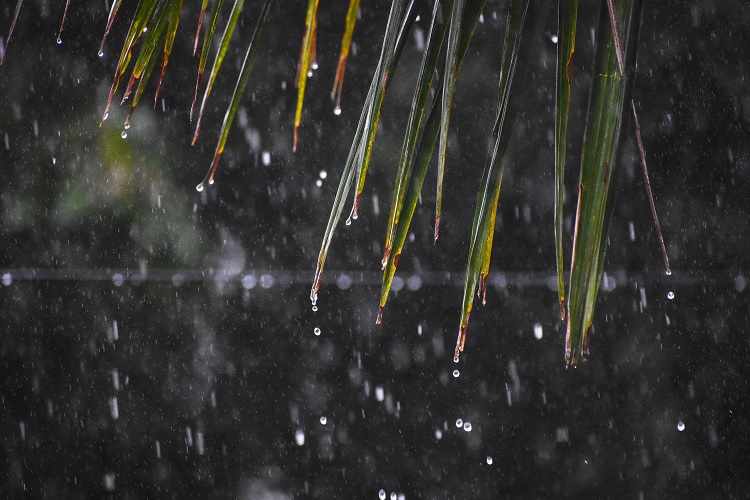
《shī》
莫名其妙的
冲动
像清晨小路边
慢条斯理享受
长着露珠青草
的野兔
突然掉头
奔向
荒草深处
隐秘的洞穴
尾巴上翘起猎犬
shī漉漉的鼻子
鹰隼在耳朵竖起的警惕上
开始俯冲
热浪
悠闲漫出地表褶皱
伴随着岩浆兴奋
在微雨清凉的
心头涌动
shī化了
一颗
心
*shī:湿、诗、师……

《你是谁》
在电脑前
我输入心中的你
键盘停下来
回车
你已然不是
我心中的
那个你
你是谁
谁是你
我心中的你
不是
你心中的我
你在电脑上
而我
又在哪里
哦,对了,今日谷雨。怪不得下了一上午的小雨。习作浣溪沙记之。
《浣溪沙》辛丑谷雨
春到池塘鸭信知
一帘谷雨读书时
浑然不记鬓成丝
斜倚碧阑词觅断
沉吟空院句难奇
野情疏阔自相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