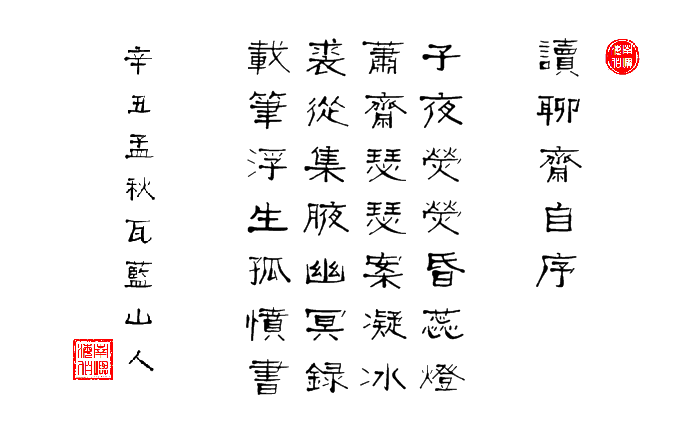一大早,就在微信群里看到小学同学发来一个故乡武汉的文章,讲的是《武汉那些年的吆喝声》。标题上写有:听听武汉那些年的吆喝声!如果有城市声音博物馆,这篇播讲绝对收藏!

常念儿时伏子酒 又闻武汉吆喝声
作者是一位武汉人,李祖勋老师。以前看过他的文章《花楼街忆旧》和《武汉那些年的夏天》,是难得的用武汉方言讲武汉生活的文章。这一篇文章,李老师不仅动手写,同时也开口录下了这篇文章。在看着文章的同时,还可以听到地道的武汉腔在耳边响起,尤其那些久远的吆喝和叫卖声,从无声的文字上是无法体会得到的。
武汉街头巷尾的叫卖声,说得文绉一点叫“吆喝声”,是从北方官话传来的。武汉人说起来就是一个字,“昂”,大声喊叫的意思。这个方言我会说,但是不知道怎么写。有些人把它写成“昂”,也不知对不对,因为许多方言似乎现在都没有对应的文字。昂字在《說文解字》中作“举也”,有高扬之意,如昂首、昂扬等。从字义上看来,肢体高扬跟声音高昂似乎也有些关联,但是昂字的读音,在武汉方言中相当于汉语拼音的第一声āng(肮)。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跟引吭(háng)高歌的“吭”字有关。由于本人对武汉方言只有语感,而没有研究,因此,姑且存疑,且待行家里手高见。
李祖勋老师列举了好多武汉那些年的吆喝声:
冰棒,美的牌的冰棒!
修绷子藤床!
破铜烂铁换花生!
洋糖发糕!
热油果回火油果醒笼包子热油果!
磨剪铲刀哇!
烧焦补锅啊!
卖印色油啊!
真丝的网子牙膏牙刷!
桂花赤豆汤!
米泡响了啊,噗!其中好多都是童年的耳熟能详的叫卖声。除了“桂花赤豆汤”以外,记得童年还有一种叫卖声“伏子酒——“。武汉的伏子酒就是米酒,江浙一带叫酒酿,四川叫醪糟。不过我不知道伏子酒的写法对不对,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伏子酒?卖伏子酒的小贩的挑着一副扁担两个筐,两头筐里都是碗装的伏子酒,上面盖一块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伏子酒。叫卖的重音落在后面的酒字上,而且声音拉的很长,老远都能听到那个酒字,就像那在深深的巷子里飘着的酒香。

记得小时候,我家保姆,那时叫阿姨,一听到吆喝,就会从三楼喊一嗓子”买酒“,然后给我五分钱,一个碗,让我去买伏子酒。一手拿了钱,一手拿着家里的碗,我飞快地从三楼跑下去,生怕卖米酒的走了。老板把扁担靠在墙上,伏子酒一碗一碗静静地躺在筐子里,上面浮着伏子酒的米团,圆圆的像一碗米饭紧紧地粘在一起,米团中间有个小洞。老板将一碗伏子酒倒到我的碗里,另外还从下面的桶里挖一勺伏子酒倒在我的碗里,作为添头,以兹鼓励。我便小心翼翼地端着酒碗往家中走去。走到中途,楼梯上无人之处,便偷偷从碗里咪上一小口,因为碗里有添头奉送,喝一口不会被人察觉。唉——那个味道,正宗的甜米酒,甜得在口中、在心里浓浓地化不开。
现在,武汉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原来的街头巷尾除了已经消失的,其余的也在消失之中,那里还有以往的吆喝声呢?跟童年一样,它们也一去不复返了。
近来几次回武汉,在小区的附近会看见骑电动车的,车上挂个小喇叭,播放现代“武普”——带武汉乡音的普通话——:“收洗衣机,电视机,电脑笔记本,旧冰箱,旧空调”,“修纱窗,洗抽油烟机”。现代人,连吆喝都不“昂”了!老把式富有人情味的吆喝,变成反复播放单调无趣的小广播了。
镜头猛地一转,到了纽约市皇后区的法拉盛,缅街(Main Street)上密密麻麻涌动的中国人中,一位老太太站在路口上,脖子上挂着的小喇叭里播放着“办护照!办驾照!办公证!办结婚证……”风雨无阻;路边摊上,扩音器响着“新鲜的猕猴桃、水蜜桃、火龙果,便宜卖”在人逢中穿梭;书摊上“最新实用英文大全、公民入籍指南、金瓶梅、肉蒲团……”的喇叭声从桥洞下飘出;还有信男信女“信主得永生”的福音在人群里弥撒;法轮大法的录音“法轮真善美,退党请登记”贴着墙边声嘶力竭的爬出。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有其特有的吆喝声。它们应运而来,应运而去,谱写了一代代的历史和传播着一声声的乡土民情。
李祖勋老师把吆喝的声波存储在磁带的电波里,记录着武汉那些年再也不能回来的声音,放进人们的时间胶囊——不意间,让我回到了那些再也回不了的日子——好事一桩!
聊斋读来开眼界 内丹修得耳中人
昨日写作课上,枫雨老师讲到读书,有人建议开一个书单。枫雨老师笑道:我料到会有人这样要求。读书因人而异,没有必读和不可读之书。不过,从她自己的读书体会中,建议各样的书,古今中外,都看一些,意在扩大知识面,丰富和学习各种不同写作风格,以便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关于短篇小说,老师觉得把莫泊桑、契柯夫、毛姆看多了,自然就学到很多短篇小说的写法。之前,我也看过许多他们的故事,但是,都以看故事情节为主。今后如果看去读,就要注意一下大师们是如何讲故事的。准备在干中学,颇有点跃跃欲试,相信一定很有意思和有挑战性。
有关中国古典,老师提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和《浮生六记》等。前两本以前翻看过,后两部近来刚刚大略领教过梗概,像快餐一样粗粗浏览一下。以后有空,还要静下心细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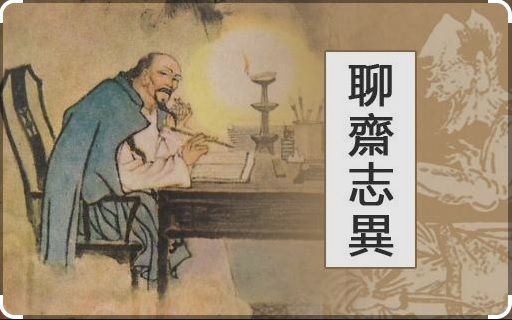
今天又看到作家莫言在分享他的读书经验。说他近来在读《聊斋志异》。问他为什么要读《聊斋》?他讲了几点。这本书里面有最为丰沛的想象力;聊斋的语言在古典文学当中最为优美;蒲松龄塑造的一系列人物极其鲜活的,极其有个性的;当然,书里边也包含了很多对社会的批判,对人物微妙感情的刻画。
今日有空,开始重读《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似乎近来有许多交集在《聊斋志异》中,加上聊斋的篇幅较短,因此,可以做日读,或者精读;《儒林外史》文长,宜于晚间闲读或者泛读。
读到聊斋的《耳中人》时,有感,便停下来。文中讲到主人公谭晋玄“一日方趺坐”,不知“趺”字的意思,于是网上去查。有注解说:就是“结跏趺坐”,略称“跏趺”,指佛教徒坐禅的一种姿势。就是将双足背交叉于左右股上,然后端身正坐,俗称盘腿打坐。据佛经说,跏趺可以减少妄念,集中思想。《大智度论》:“诸坐法中,结跏趺坐最安稳,不疲极,此是坐禅人坐法。”
可惜,我大概此生与佛无缘,因为我腿足生硬,弯曲不得,尤其不能盘腿,更遑论”双足背交叉于左右股上“。记得当年跟李洪志信徒学修法轮大法时,也是由于不能盘腿,以致最终没有修成大法。故而心中妄念甚多,难以集中思想,常有疲乏之感。不知练习瑜伽是否由用?
文中还提到“谓是丹将成,窃喜。”这个丹,让我想起前日在工坊云端上的一堂“内丹生命观与文艺创作”课,由浙江大学的一位孔教授讲授。其中就讲到这个“丹”。炼丹是道教法术之一,原指在炉中烧炼矿石药物,以制“长生不死”的丹药,即“金丹”。后来道士将这一方术加以扩展,称“金丹”为“外丹”,称精神修炼的成果为“内丹”。人体比拟鼎炉,“精”、“气”比拟药物,以“神”去烧之,使精、气、神凝成“圣胎”,即为“内丹”。《耳中人》的主人公此处就是炼内丹。
如果说,内丹可以治病、养生,我都觉得可信。但是说到内丹可以超越死亡,或者说长生不老,我就开始质疑了。但是,孔教授提出:你不能证明你不知道的就是没有的,科学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由错误到进步的一个过程。并提出类似法轮功李洪志的说法,科学不能证明的不等于不存在,人和神是处于两个不同的界面,人怎么知道神或者另一个界面的事物呢?
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见过宇宙黑洞吗?我们看得见暗物质吗?我们能理解三维空间,那么四维五维六维呢?人类的认知虽然在科学技术手段帮助下,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是仍然是有限的,比如宇宙的起源,比如上帝是否存在?
因此,以往的经验论和“眼见为实”的判断方法,已经不能有力的解释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了。据此,虽然我们仍然对没有证据表明的东西习惯地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没有见过和没有证明的东西。哲学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怀疑,并且从怀疑中探索事物的本质或者真相,而不是轻易的肯定或是否定。

那么,我们一个如何看待那个“长三寸许”的耳中人呢?信还是不信?
得小诗一首,《读聊斋自序》。
子夜荧荧昏蕊灯
萧斋瑟瑟案凝冰
裘从集腋幽冥录
载笔浮生孤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