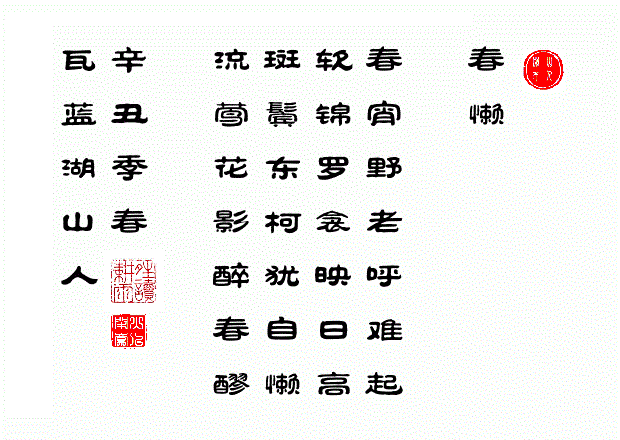四月刚过半,往年这个日子,应该是每年缴纳国税的截止日期。在还没有纳税软件(电子申报表)的时候,邮局这天往往会延长开门时间。因为邮局里面会排着长队,挤满了那些不到最后一刻不交税的人,等着邮局在他们的邮件上盖上4月15日的邮戳。我想,他们当中大概多半是要缴税的,所以才拖到最后一天。像我这样年年退税的穷人,早早就把税表上交了,高高兴兴地等着国税局的退税呢。
不过,今年情况特殊。由于疫情的原因,国税局有告示:财政部,国税局将缴税截止日期延长:个人纳税日延长至5月17日。因此,我也就一直懒着,到今天才想起做税表的事。
微信里看到文友一篇“劳动节说‘懒’”的文章。说的是早上“迟起”的懒,而不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懒”。从梁遇春的文章《“春朝”一刻值千金》讲起,还聊到杰罗姆的文章《懒惰汉的懒惰想头》。劳动节说懒,倒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梁遇春,何许人也?《维基百科》有简介:梁遇春,福建闽侯人。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1928年秋毕业后曾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翌年返回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后因染急性猩红热,猝然去世。
其作品主要为散文与翻译西方文学作品。1926年开始陆续在《语丝》、《奔流》、《骆驼草》、《现代文学》、《新月》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后大部分收入《春醪集》和《泪与笑》。
今人评价,梁遇春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师从叶公超等名师。其散文风格另辟蹊径,兼有中西方文化特色,被誉为“中国的伊利亚”。同时,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被忽略的角色,在短短27年的生命里,他只给我们留下了37篇小品文和二三十部译作。
文学史家唐弢在《晦庵书话》里指出:“我喜欢遇春的文章,认为文苑里难得有像他那样的才气,像他那样的绝顶聪明,像他那样的顾盼多姿的风格。每读《春醪集》和《泪与笑》,不免为这个死去的天才惋惜。”
梁遇春的文章从没有拜读过,主要是因为我“懒”而无知,加上他被忽略的角色和早逝。这反倒让我有了读读他的《春醪集》的念头,欣赏他“一流的散文”和他“如星珠串天,稍纵即逝”的文思。

“现在春天到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五六点钟醒来,就可以看见太阳,我们可以醉也似地躺着,一直躺了好几个钟头,静听流茑的巧啭,细看花影的慢移,这真是迟起的绝好时光。能让我们天天多躺一会儿罢,别辜负了这一刻千金的‘春朝’。”梁遇春如是写道。
依着我的基因,我天生赞同梁遇春的“迟起”一说。尤其是在退休前,遇到周末,恨不得一觉睡到正午才起床。但是,我不会在床上“醉也似地躺着”,而是云山雾罩中,呼儿嗨呀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不过,退休以后,天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迟起”,日子却反了过来。现在,每天逢日出而起,必沐浴朝阳散步。即便是睡意朦胧,也会在散步途中“静听流茑的巧啭,细看花影的慢移”。看来,杰罗姆在《懒惰汉的懒惰想头》(Idle Thoughts of An Idle Fellow)一书中所言极是:“闲懒和吻一样,当它被盗走了之后,它的味道才是甜的。”
只有当我天不亮就爬起来,匆忙赶着上班时,才会体会到“迟起”的美。只有上班途中坐在地铁上,当我迷迷糊糊半睡半醒时,才会感觉“迟起”跟美女的吻一样可爱。一旦退休,不用上班了,“当你无事可做时,空闲就变得一点也不有趣,”于是,人们便要用“早起”去打发无聊的空闲。
可惜梁遇春英年早逝(1906年-1932年),如果他活到我这个岁数,抑或是活到杨绛先生那个年纪,不知道他对懒人的定义还是否如此:“世上最懒惰不过的人们是那般黎明即起,老早把事做好,坐着呆呆地打呵欠的人们。”
黎明起来后,虽然不上班,却似乎终日里总是忙忙碌碌的。早晚锻炼身体,白天读点书写点字,当然,还有做不完的家务事,哪里有“坐着呆呆地打呵欠”的时间?戏作七绝一首记之。
《七绝》 春懒
春宵野老呼难起
软锦罗衾映日高
斑鬓东柯犹自懒
流莺花影醉春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