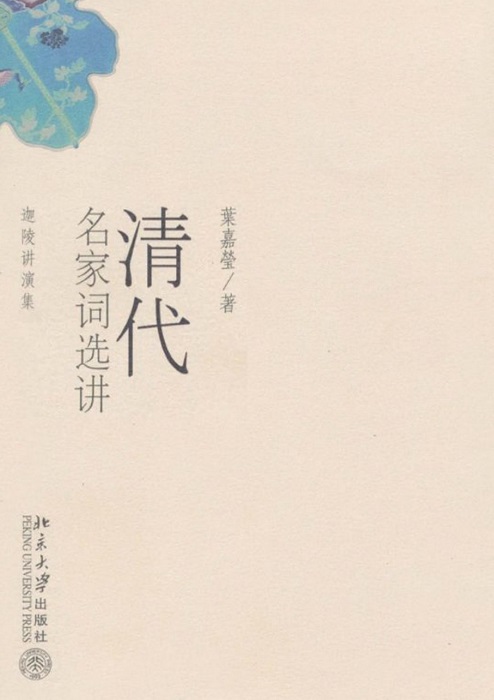昨日潇洒了一回,随心所欲的从长篇回忆录跳到【清词丛论】的纳兰性德。今日收心,重游王鼎钧公的【怒目少年】。
读了一天书,到了晚间,换换脑袋,看看新闻。

成龙,影坛资深巨星,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不过,他一直不用通信软件、没有微信帐号,因为他觉得在手机上最浪费时间。因此,他在央视节目“鲁健访谈”时,感叹自己和年轻人的语言脱节,现在年轻人讲的话他都听不懂。
成龙表示宁愿多把时间放在思考上面,看些好电影、听很多歌、把国语学好、多读诗词、看些有用的东西,多开会弄些好的剧本,多练功,其他就希望世界和平,每个人都能健健康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只要不妨碍别人、违反公德和法律,就行。其实,作为同辈人,我倒是很赞成他的一些活法:看些好电影、听很多歌、多读诗词、多把时间放在思考上面。不同的是,我每天都会看手机,时间不定,一般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即使这样,仍然是跟年轻人的语言脱节。这是代购,也是当下科技发展给我们这代人带来的淘汰感。
当下的科技发展已经到了人工智能(AI)时代,开始代替许多以前的人工操作。微软支持的OpenAI去年11月开了科技竞赛的第一枪,将其开发的AI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开放给大众使用,开放2个月内的月用户达到1亿,成为史上成长最快速的App。
就如同不管你是否使用手机,手机已经成为仅仅次于人类第一需要的吃穿住行的工具。手机有利有弊,譬如成龙就认为浪费时间。但是多数使用者还是认为利大于弊。那么,AI呢?

杰弗里·辛顿 (Geoffrey Hinton),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被广泛认为是“AI教父”。为人工智能领域做出了许多贡献,是第一个证明使用深度神经网络进行语音识别的有效性的人。
辛顿最近离开任职10年的谷歌,为的是要大声说出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而不致影响前东家。众人皆知,辛顿在谷歌的工作对AI系统的发展极为重要。
辛顿在接受路透访问表示,“我不会贬低气候变迁,我不会说‘别担心气候变迁’,那也是很大的风险。但我认为AI也许更急迫。针对气候变迁,建议要怎么做很容易:只要停止燃烧碳。如果照做,最终不会有问题。但针对AI,还不清楚该怎么做”。与此同时,许多科技界领袖公开对AI可能造成的威胁表达忧心,包括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Elon Musk)。
我想,他们是内行,其担心必有道理。我不知道的是,人类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是否会被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打败,就像谷歌的机器狗可以打败人类的冠军棋手一样。目前对此众说纷纭,我们一般人还看不出端倪。
不过,一旦这种事情发生,那也没有什么。正如人类有生就有死一样,既然诞生了,死亡就不可避免。至于怎么死,死于机器人、地球冰川的另一个寒武纪、地球爆炸、外星人入侵,那都是人类未知的未来命运。
正如庄子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一切都似乎很遥远,至少我们这辈人是看不到了,虽然,我很希望看到。
纵然活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在地球和宇宙之间,也不过一瞬间而已。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的使命就是:快快活活地过好当下,足矣。
05/06/2023 周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