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发小讲起一件我们小学的往事,让我那些早已尘封的过往,竟然被搅动得沉渣泛起。
他说的是小学六年级的1966年,彼时正值WG开始。我们“革命小将”参加了史无前例的“革命”,革教育界“资产阶级一统天下”,尤其要革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我们也要采取革命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批判以往老师对我们管教太严,对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这一段情节我在【荒唐的真实】一文中做过简单的叙述:
我们的“大鸣大放”,就是照搬报纸上的宣传,批判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被罢官的“海瑞”,还有那个不知道是怎样反党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我们的“大字报”,就是把课堂上临摹柳公权、欧阳询、颜真卿的“真迹”,发挥到大白纸上,铺天盖地地贴满教室和学校楼道的墙壁。我们的“大辩论”,就是质问老师和校长,为什么执行资产阶级“旧”的教育路线,把我们“革命小将”培养成为俯首帖耳的“小绵羊”?老师和校方如果辩解,我们就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这是首文革早期流传很广的造反歌曲。唱到末了“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还要在结尾处加上呐喊声:“杀!杀!杀——嘿!”以渲染加强气势。
大概是属于战后婴儿潮的缘故,我们那时班上的学生很多,记得至少有50多人。记得高年级我们的教室里的桌椅,面对前方的黑板讲座,按三个纵队排列,每个纵队一排宽为两个课桌,长有八九排课桌不等。我们班主任为了管理我们,不知从哪里学的,建立了一整套旧式“保甲制度”。
现在的人们恐怕对保甲制度不太熟悉,保甲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国开阡陌,编什伍,实现连坐制,其基本形式为10户为“甲”,10甲为“保”。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沦陷区推行了台湾的保甲制度。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仍在使用。看过电影《抓壮丁》的人,就会记得里面有个讲四川话的“王保长”。解放后,新中国废除了保甲制度。我们那时的老师,大约三四十岁左右,多半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文化人”,想必是经历或者至少是了解“保甲制度”的。
我们在低年级(一二年纪)的时候,一个班的班干部,除了班长和班委会的学习委员、文体委员以外,还有三个组长,各自份管三个纵队。他们的任务好像就是帮老师收发作业本这类的“工作”。后来到了三年级时,大部分同学满了九岁,加入少年先锋队的年纪,于是开始出现了戴红领巾的少先队的干部。不过那时候入队很不容易,不像现在,一进入小学,是个学生就可以入队。个个都佩戴红领巾,哪里还有一点“先锋队”的样子?我们那个时候,要表现非常好才能加入少先队。像我这样的,怎么“努力”都不行。直到四年级,所有同学都到达入队年龄,我经过一年多的“组织考验”,好不容易才加入。
说完了桌椅的具体摆放,介绍完了班干部组织结构,开始谈正事——“保甲制度”。
自打上到小学五年级,换了一个班主任,朱老师,她一直带我们升到六年级直至毕业。到了高年级,我们就是小学里面的“大哥大”,胆子也壮了,心也肥了,也混成老油条了。加上每年都会从高年级插入几个留级生,班级开始不好管理了。像我这样的,属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主儿。打架斗殴、校园霸凌,均不涉及,但是生有”课堂多动症“。老师讲课时,一旦以为听懂了,就忍不住精神不集中了,不是跟旁边的同学讲悄悄话,就是前后左右乱动,打扰其他同学,妨碍课堂纪律。当然,班上不守纪律的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大概我算是比较突出的吧。
我想,朱老师肯定不只是为了针对我,而是从全局战略性的管理部署出发,将原来的一个纵队一个组长的干部管理结构,细分为前后两排的四个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设“小组长”一名,原纵队组长升级为“大组长”。这样每个小组长就可以很容易地“监督”和“管理”身边靠得最近的同学,将他们的言行和一举一动放大在显微镜之下,让他们无所遁形。小组长向大组长负责,这样大组长则通过管理该纵队的几个小组长,轻松地完成以前看管不过来的十几个人。而班干部只须抓好几个大组长,就可以纲举目张地管理好全班。至于黄雀在后的班主任,则可以游刃有余地从班委会和大小组长的管理中,掌握全班的大体动态和每一个蛛丝马迹的细节。一张无形的大网——“保甲制度”就这样笼罩在我们身上。

组织落实后,管理方法也要跟上。老师规定,每个小组长都要用个小本本记录每天本组同学的课堂表现,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及时汇报班主任。到了周末,召集小组长以上班干部,包括少先队的干部开会,汇报一周各小组同学们的课堂表现;根据小组长的详细汇报,加上老师的评语写成本周品行表现报告;然后由小组长和班干部将报告送至家长;家长看过后,还需签名或盖章,表示知道了“已阅”,最后由学生下周一交还老师,作为学期末考评的依据。这套管理方法将学校管理跟家庭教育丝丝相扣,环环相套,颇有些像天兵天将撒下的天罗地网,纵有孙悟空齐天大圣七十二变的本领,也难逃法网。
而且工作抓重点,“枪打出头鸟”,着重打击几个调皮捣蛋屡教不改者,其中就有我。从小在老师的眼里,我就是个调皮的小刺头,而且头生双漩,脾气倔强。我是一只顺毛驴,你对我好,我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若是谁侵犯了我,我绝不善罢甘休。一年级时,为了保卫同座的同学不被前排的同学欺负,我曾经从书桌上抓起一把铅笔,插向前排同学的后脑勺,险些造成重大伤害,现在想想都后怕,幸而没有弄出大事儿。几乎一上学就被学校开除,后来考虑到事出有因,并不是我欺负同学,而是属于类似“防卫过当”的性质,遂改判为休学10天,以观后效。这是我在小学中判刑最重的一次。
这些都在【一支铅笔的故事】有详细记载。自此,从一年级就劣迹斑斑的我,一直都受着历届老师“以观后效”的监督。
一般的同学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到这张大网的厉害和威力,应为他们不常常犯事儿,而我是重点被管制的对象之一,深受其害,故而至今回忆起来,感觉仍然是苦大仇深。
不能不说,今天看来,这种细化了的组织形式“保甲制度”,加上学校和家长双重的管理方式,还是很奏效的。一些“坏学生”可以不在乎学校和老师的惩罚,但是多半怕受到家长的惩罚。比如我家老爷子的管理是很严厉的,“文斗”如果不解决问题,就采取“武斗”形式。故而,我对老师搞的这套“保甲制度”,并派同学向家长来报告我的“罪行”,致使受到家长的镇压,非常反感。以至于到了WG革命造反之时,我们将班主任的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统统都用大字报的形式,粘贴到教室和学校走廊的墙壁上。不过这是后话。
那个时候的小学,同学之间就知道男女“授受不亲”。若是男女同桌,通常在桌子中间画一条“三八线”,楚河汉界互不侵犯。谁要是过线,就会被对方用胳膊肘怼回去。我的小组长是一位姓H的女生,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当过班干部,这次实行保甲制度,是她第一次进入干部队伍。平时,大家男生和女生互不来往,井水不犯河水。
我虽然调皮,但是学习还可以,关键是我跟同学们关系很好,小有人缘,故而同学们选我做了个“一条杠”的红领巾小队长,统领着一个十来个男生组成的少先队“第一小队”。虽然班上还有“两条杠”中队长领导,甚至还有“三条杠”的大队长领导,不管这么说,咱大小也算是个干部了。
自打H女生当了组长后,虽然咱不当回事儿,可人家工作认真负责,咱也没的说。不久,在一次周末的干部会上,H组长翻着她的小本本,历数我从周一到周六,哪一堂课讲了什么话,哪一堂课回头跟后面的同学交头接耳,哪一堂课在桌子下面偷偷玩东西,哪一堂课做完了作业,看窗外的小鸟,事无巨细一五一十地汇报给老师。这可让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平时不声不响的H组长还有这样两刷子,这不就是个身边出现一个卧底的间谍吗?我不记得曾经得罪过她,如果有,顶多就是有时候她问我一些比较迟钝的“学术”问题,我没有耐心解答而已。不过,那也不至于就把我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到全体班干部和老师面前啊?
直到后来,经历了WG,我开始发现人群中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没有本事,一旦有机会,却以整那些比自己优秀的人而泄愤,发泄平时被压抑的情感。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就跟我采取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一样,其实无可指责。就跟世界上有白天黑夜,人有善良和邪恶的,聪明的愚昧的一样,用苏东坡的一句诗,叫做“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现在是明白了这个道理,看淡了,看穿了,不会再跟那种人计较。
但是,当时我才是个小学生,而且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的反应是受到不明攻击,被人出卖了,立即回击。现在想来,如果要讲道理,还不是我“违规”在先,咎由自取。不过,那时候不可能有现在的认识,只凭一时的基因本能冲动而行事。
我的回应是,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第二个周末,我的小本子上也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小组长的违规言行。谁能做到像圣人和上帝一样从不犯错呢?是个人就有缺点和错误,只要留神,鸡蛋里可以挑出骨头,只要有心,芝麻里可以找到西瓜。在周末的干部会上,我第一个举手发言,首先虚晃一枪,先把自己打倒,说自己本周犯错最多,并作深刻检讨。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反正我是坏得有名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然后,正当老师吃惊之际,将矛头指向H组长,“第二个就是她”。打开小本本,一条条列举H组长的一周的“罪行”。你想以整我立功受奖,没门儿。今天我也把你的“罪行”公布于世,用武汉话讲,叫做“大哥莫说二哥,脸上麻子一样多。”我死了,你也甭想好活,大不了,同归于尽(反正我也死了)。这种牙呲必报和胡搅蛮缠的突袭,将H组长弄得面红耳赤,怔在哪里,嘴里不知嘟哝着什么,半天下不来台。
班主任老师看到这里,算是明白过来了,但是又将我没有办法,我已经批判了自己,对H组长的揭发又是有根有据,只好将两人的报告都写黑了。我这一招歪打正着,自此一役,H组长知道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汇报的,再也不在会上公开记我的“现行”了。不知道私下里是否采取偷偷向老师汇报的行径。如果被我知道,那时的我,一定会伺机用各种方式回击。三年级我就读过水浒,家里的三国演义,断断续续地翻看过多次。虽然没有诸葛孔明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但是一些春秋兵法常识如“欲擒故纵”、“釜底抽薪”、“混水摸鱼”、“趁火打劫”等等,还是知道一些的。总之,这次通过“反客为主”,“声东击西”了小组长,我无意间打破了“保甲制”的底层基础,因而脱离了最紧身的桎梏,从而多多少少在夹缝中获得些许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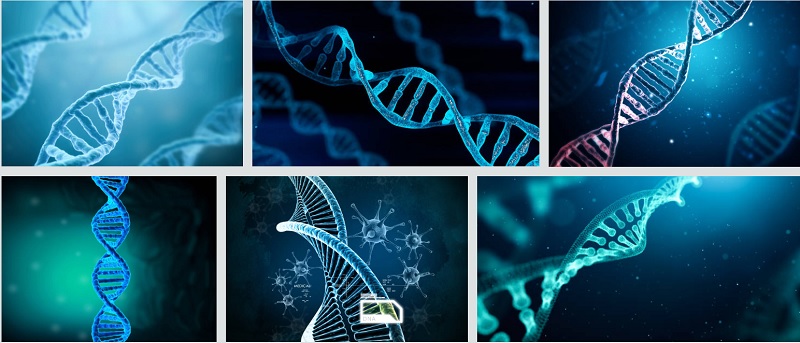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小时候读【三字经】,开篇就是这几句。大意是说,人在刚出生时,本性都是善良的,性情也很相近。但随着各自生存环境的不同变化和影响,每个人的习性就会产生差异。人性真的是善的吗?有人提出疑问,还有人否定。“善”和“恶”的双方都有许多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观点。似乎至今没有定论,这是人类目前无法用科学方法证实的。
暂且不谈本性善恶一说,单说人的本性由什么决定的,也有许多解释。我比较同意基因(gene)说,即是天生的,又是遗传的。这个看法基于人类对细胞、染色体、DNA与基因的科学认识。人的本性主要由“携带遗传信息的基本物质单位”基因而定。人们发现,基因在遗传过程中会发生突变,使得问题跟更为复杂。那么,为什么人类会通过遗传衍生?为什么遗传过程会发生变化?这些涉及“我是谁”的根本问题,似乎超越了人们目前的认知范围。
既然找不到答案,人们只能通过观察到的现象发现,人的本性应该由先天的因素决定,不管是善还是恶。“苟不教,性乃迁。”三字经又说道。也就是说,外界或后天的环境通过“教”的方式,将人之初的那个“天性”改为世俗的“陋习”。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就是社会将人性(自由)“约束”了。从个人的天性上来讲,社会就是个约束,不好。从人类整体(集体)的发展来说,社会的约束有利于人类的进步,有必要。因而,个人和集体的矛盾将在人类社会中永远存在。我们的基因也在“必要”的禁锢中,“天生”地要永远与之抗争,或被压抑,或者有所突破,大不了就是“不自由,毋宁死!”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并没有打破班主任的“保甲制度”,其实也打破不了。一个顽童飞蛾般的幼稚挣扎,在成人制定的教育体制里,充其量只是孙悟空率性的大闹天宫,获一时之痛快,得些许自由,然而,终究会被如来佛一巴掌镇压在五指山下。
大概正是因为如此,WG一来,我们被压抑的天性像放出笼子的野马,肆意地践踏过去所谓的“牢笼”,校规班纪,去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天时地利人和,那叫一个痛快!
岂料,有人正是利用了我们这一点,才将当时的神州大地一下子闹了个天翻地覆。
半个世纪后,耄耋之年,坐在灯下回顾儿时往事,叹昔日的四射的锋芒,已被社会磨蚀殆尽,只剩青埂峰下一块圆润的顽石。一辈子,就这样走过来,时间不可逆转。唯有骨子里的基因仍然顽固地不服气,“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天生的!可笑,可叹,可悲,可喜!
*自打小学毕业一别,似乎此生再也没有见过我的H组长。只是听说她在中学时候,曾经参军入伍。几十年后回国的同学聚会上,也没有见过H组长,同学之间好像也不知道H组长的行踪。如果有缘相见,我会告诉她,我早就对此释怀了,也不会怪罪她了。难道当初我就没有错吗?但愿我们从中汲取教训,在今后的人生中,以我佛慈悲之心,宽以待人,在纷扰世事中调伏自心,将对于他人的艾怨修炼为自己内心的柔和清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3/18/2024 星期一
